
《眩晕》的主人公是一个怀揣电影导演梦想的北漂。但这个梦想是孱弱的,不等他人来施压,他自己便先行解构了它。没有人给他明确的打击,没有事情让他有鲜明的挫败感,然而几乎每时每刻,面对任何事情,他都是虚弱的,失能的……祁媛的写作为我们展现了那些未老先衰的青年的某种典型形象,他们怀着莫可名状的伤痕,心不在焉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他们行动能力极其微弱,内心活动却过分丰富;他们的亲情千疮百孔,爱情暧昧可疑,对任何事都缺乏激情……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因为他们只会眩晕,只会疲惫,因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已经老了。
编辑推荐
* 八零九零后一批青年作家群体愈发受到关注,他们已成长为日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窈窕文丛”精选八位风格鲜明、颇具潜力的年轻女作家集中亮相:孙频、周李立、朱个、阿微木依萝、池上、庞羽、余静如、祁媛。
* 她们的写作多从自我经验出发,从生活细节出发,源自天性和本真的思考,呈现出新一代独特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
祁媛,1986年生人。201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同年开始小说创作。小说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先后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 第四届郁达夫中篇小说提名奖 ,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具潜力新人奖”提名,“2016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
精彩书评
在祁媛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一种冷峻的观察如何和肆意的独白非常自然地混融成一体,仿佛时时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位小说书写者所受过的现代绘画的训练,她写小说就像在画她喜欢的素描,用锐利的眼睛捕捉到光影明暗间的实在世界,但落笔的每一根线条又完全是自我的,是不管不顾众多规矩限制的。
——张定浩
主人公精神世界中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世俗价值的质疑和诘问——这构成了祁媛作品特有的精神维度。在渗透着忧郁诗情的同时,文本内还镶嵌着不少浮世绘式的画景。
——王宏图
目录
1 眩晕
55 跟踪
101 翻车
127 黄眼珠
151 桥洞里的云
223 美丽的高楼
精彩书摘
眩晕
一
如果这个女人不是熟睡着,他是无法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她的白发的。她头发上端染的栗色里透着灰调子的橘红,有种蓄意的人工风韵,而根部却在静静地泛白。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渐渐照亮了屋里的白墙,被子床罩也都是白的。他一时想不起来昨晚那场乱糟糟的做爱持续了多久,她还在继续睡,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于是他斜过脸来,仔细地看着她。他还从没这样毫无顾忌地看过她。
那些白发是新生的,与染过的发色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更白了。他想到某种硬壳虫被踩烂后溅出来的白浆,黏稠得恶心。那些白发生长得很旺盛,色泽纯粹,一味雪白,他想起去年老家的大雪,那是他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整整下了两天两夜,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埋掉。一星期后,雪才渐渐融化,但背阴里的积雪,很久后才慢慢消失,如此的慢,以致院子里的桃花吐蕊的时候,雪还在那儿待着,变成了冻雪,冻雪是睡着的雪,是死了的雪。他又看了看她发根的白发,觉得那种白不是睡着的,它们在醒着,在生长。
他觉得白应该是新生的颜色,里面没有苍老衰败,梨花、辛夷、腊梅,是新嫩的,可是一显露出来之后,好像就开始变老了。头发根部的白发也是白,但无论如何扯不上是新的,想到这,他有点发呆。他忽然想到自己,聚精会神地体会着自己的头发,尤其是头发根部的动静和色泽,想到自己的头发会不会也一点一点地在由黑变白,但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可笑。
眼前老女人的睡相实在丑。一脸的松肉耷拉着,眼睛半翻,好在没朝这边看,否则会以为她根本就没睡,或者死了。人死了,眼睛大多半睁,好像怕人虐尸,或者担心别的什么,鬼知道!他想到“海棠春睡”,“睡美人”,这位可不是什么“睡美人”,而是“睡老人”,他不由邪僻地笑了一下,他想到在哪里看到过“睡美人”的英语,于是努力在记忆里“百度”,结果徒劳,心里暗自骂了一下。
很静,他有足够的闲暇胡思乱想,天马行空,这也算是一种休息,一种都市人奢侈的休息。可他实在天马不起来,转来转去,脑袋里都是眼前的这个翻眼呼睡的老女人。他想到上小学时去同学家做作业,进门,撞见地上横着同学的爸妈在午睡,他看到同学的妈妈裤衩私处部位被什么东西顶起,分明是个小鸡鸡,女人也长鸡鸡?他顿感惊恐,接下去的作业也弄得错处连篇,一塌糊涂,他想到不久前的一个异象,就是家里唯一的鸡,一只老母鸡,忽然半夜打鸣了,他被吵醒,细细品味着那一阵阵的叫声。后来那只母鸡也就不再下蛋,结果被母亲宰杀了。他侧过脸去再次打量着那个老女人。收回目光,他有些疲倦地望着乱乱地盖在身上的白被褥,发现被子大半被她裹了去,但女人的肩膀尚露在外面,肤质灰暗,有个形状模糊的暗紫色胎记,像半个蝴蝶的翅膀,又有点像一个面具。此时,忽然他发现她在看着他,不知何时她已经醒了。她在打量着他,抬身凑了过来,抚摸着他,不一会,他们又做爱了。
她有节奏地蠕动着,眼睛微合,唇缝微张,无疑是在享受着此时的快感。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给人提供快感”的角色了,但还是忍不住把视线从发根的白浆色移开,后来干脆闭上眼睛,可是那白浆色已经牢牢地渗透了他,就算不看,脑袋里也全是她的白发。他渐生一种幻觉,感觉她整个头发瞬间变成了白的,并随着那个“蠕动”而轻微地颤动着,飘动着,散发着死亡般的苍老,他感到自己在和一个百岁老女人做爱,有点害怕了。身下的那“白发女”这时张开了微醉的眼睛,并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因此眼神慢慢变得硬了些。当他的目光和她碰上的时候,他迅速可怜地顺下了自己的眼睛,不得不继续埋头苦干,这样又过了一刻钟,他终于听见身下传来古老的满意的呻吟,心里一松,想这下差不多了吧,于是小心翻身下来,径直躲进厕所。
早晨的微光环绕在白色的马桶圈上,朦朦胧胧的像一道白光环。他看着自己的尿液喷溅在马桶里,被窗外灰色的光映照得一层一层荡开,他想起了小时候爱唱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破浪……”这时她也冲进了洗手间,屁股还没有坐在马桶圈上,哗哗的尿声就响起了,他还没听过如此明亮的尿声,有点像乡下的牛羊,这时他感到有一些尿珠子溅到他的腿上,低头看,那尿珠子已在瓷砖地上形成涓涓细流。她抬起头看着他说,你刚刚怎么回事,心不在焉的,想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觉得一阵尴尬,好在她并未逼供,心思也好像转移到另外一些事了。尿完以后,她蹑手蹑脚地绕开地上的尿流,走出了洗手间。
二
他第一次听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学校讲座的时候,没想到两人会因为一张名片发展到上床这步。说实话,第一次和她做爱的时候,和这个比他身份地位都要高许多的老女人做爱的时候,感觉怪怪的,毕竟她比他大二十多岁。看着她浑身价格不菲的衣饰,精致的妆容,还有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他听不懂的英文和法文的单词,他的自卑感就溜了出来,但是,当他把光溜溜的她压在身下时,便发现她和以前上过的女人,老家村里的那些女人,甚至和妓女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她老,皮糙,人丑。他感到了自己的优势,年轻的优势,性的优势,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战胜自己贫穷卑微的心理,战胜自己的屌丝身份,他看着身下俨然已经被他征服的属于另一阶层的女人,感到自己不是在搞她,而是在搞这个高于他的阶层,甚至在搞近来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世界。
他已经记不清楚和她总共做过多少次了,十二次?十五次?这样想时,他发现“次数”并没有什么意义,数字而已,他也不想用“机器”感来形容,但除此之外,他找不到更确切的字眼来形容了。除了这个女人的资深制片人和影评家的身份,他对她身体上的一切都充满厌恶,她的平板肥脚,稠密粗硬的阴毛,还有有时会显露出来的微微的胡须,这些都让他难以忍受。
她定期给他打电话,一来就上床。虽然他也处在荷尔蒙贲张的青春时期,但面对一个老女人,他其实更想和她谈电影,但是,怎么说呢,什么话题呢,“探讨”些什么呢。她人中部位的稀落的硬汗毛表明她性欲尚未衰退,她的动物般的眼神,哎,别提她的眼神了。记得第一次单独见她时,倒是真的想求教于她的,当时在她的旅馆房间,沙发,台灯的温暖的光,她在吸烟,一根昆烟,这本是可以谈电影的氛围。他提了几个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及别的他所心仪的导演,比如,他很想谈谈法国的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狂人皮埃罗》和加缪的《局外人》的关系,还有意大利马里奥·莫尼切利的《警察与小偷》的小说原型,但每次开口时,他感到她并没有兴趣,听得心不在焉,而且分明是一个资深影评家在听一个小毛头胡扯,嘴角也不时露出有点鄙夷的冷笑。有时她开口了,可多半是顾左右而言他,比如抱怨酒店里茶叶的劣质,空调的噪声,屋外建筑工地的大声喧哗,然后,她望过来的目光就变得晕晕而火辣了,电影的谈话即刻演变成浪潮般的床上运动,重复而又重复,具体的肉欲,肌肤的接触,怎么也无法和刚才的话题相联系了,而且在交媾中,他毫无快感,常做到一半,他就蔫了,而她依旧兴致勃勃。
有段时间在北京,他完全陷入了困境,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逃不出的困境,深夜醒来失眠,开始掉头发。他大概想要在黑暗中伸手抓住些什么,仿佛抓住了光,又仿佛什么也没抓住。要是什么事都不做,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他好像被一股力量牵引着。他不知道这力量究竟是什么,来自哪,又将带他去何方。每次照镜子,他都感觉身上在发生着一些什么,又像一切都没有变。他的房间整整一面墙,贴满了他崇敬的导演和作家的照片。无数次他在黑暗里凝视这面墙的时候,他想到了灯塔。这面墙是他的灯塔。曾经有一个女孩问他为什么来北京时,他没有道出他的野心,只说喜欢北京宽大的马路和人来人往。确实,在很多时候,他会在大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下来,或者在天桥上停下来,看着那些无数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他喜欢人群,另一方面,又讨厌人群。
三
有一个女人倒是总和他谈电影,每次都谈得眉飞色舞,满脸通红的,但他却完全不想和她谈。这是因为他有点瞧不上她。
他是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这个女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却记不太清了,能记住的是那天晚上他不知怎么了,也许是无聊,更多的是不安,其实就是想搞女人。从微信上的头像看,她有点像张馨予,又有点像李小璐,反正就是一张网红的脸。他加了她为好友,然后就聊了起来,没聊上几句就约见,对方竟然也立刻答应了。当晚见面时,他发现她和微信上的头像差距巨大,不仅脸大,而且相貌平凡,皮肤也不嫩,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她开了房。
她是商场卖女性内衣的,她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答是电影编辑。她不懂电影编辑是什么,但“电影”是懂的,在她的眼里,凡是和电影沾边的职业,就和导演差不多,因而认定“电影编辑”这个工作是极其牛逼的高尚职业。她会把自己概念里的所有当红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影星和所有相关的八卦,全部与“搞电影的”联系在一起,而且认为所有电影界的从业人士在社会阶层上也高人一头。因而,她很自然地把“他”视为非凡人物了。
想来,他倒是很愿意有女人把他当成“电影导演”那样供着的,他需要这种虚荣,可他知道这种虚荣一捅就破,比如,女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位电影导演没什么钱,除去日常开销,偶尔累了才去喝两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显得吝啬。他总是有危机意识,不止一两个女朋友抱怨过他的小气,但他觉得无所谓。
近来他的电影导演野心似乎不如最初那么强烈了,另一种相反的东西,正悄悄地咬噬着他对电影最初的那种“崇高”感。这让他担心,怕自己忽然有一天会对自己宣布:电影是狗屎,我不干了。他寻思着这个心理变化是从何日开始的,这其中缘由颇为繁杂,一时也理不太清,但他需要弄清楚。于是他不得不把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和热爱的来由,像过电影一样地过了一遍。
高中的时候,他觉得电影真是一个神秘牛逼的世界,那里面的人总是格外的鲜亮时尚,电影里面的事哪怕是个屁,也比现实要精彩得多。他常逃课,躲到录像厅里去看电影,看得昏天黑地,同班同学有个胖子,出生于富裕家庭,有DVD,他总是以去他家做作业为名看碟片。只要他稍有零钱,就去镇里那家光盘店里买碟片,他已经数不清看过多少部电影了,总有几千部吧。他觉得自己离不开电影,甚至觉得电影电视剧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现实生活,比如他自己的生活的目的,睡觉,吃喝,上学读书识字,都是为了能观赏电影而已。终于有一天,大概是高二的时候,他忽然认为:只要他再继续看下去,总是可以成为导演的。他不知道这个自信从哪来,但很明确,似乎是个“启示录”,就是他必定会成为导演的,一个牛逼的导演。
高三的时候,他决意报考电影导演专业。从高校的简介里,他发现电影导演专业比较冷僻,也就是说一般省立的大学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只有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比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等,才设立这个专业。他决然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可惜,两次考试,两次落榜,而且是在初试的时候就被刷下来了,但这并没有打击他的梦想和信心。他想到那些励志的电影,觉得考试的失利,不过小菜一碟,根本没有什么,于是在信心满满的状态中又考了一次,终于被北京一所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导演专业录取。
他并不太满意,因为到了北京后,他发现“师范学院艺术系”毕竟是三流院系,业内人士并不太认可,可离他的导演梦,无疑还是大大近了一步。但事情并没那么顺利,原因是学费太贵了,到第三学期的时候,家里就负担不起了,可让他放弃又是不可能的,于是休学一年,去赚钱交学费。好在他年轻,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而且呢,这时他又想到了某些励志的电影,心里变得平静了。
算起来他打过好几种工,跑过外卖,发过传单,做过促销,有一次居然还跑到一家桑拿中心里做服务员。这使他开了眼界,认为这一切经历迟早会成为他的导演梦的本钱,他模糊地记起不知在哪里读到的一句话:“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的上帝。”
后来经老师介绍,他接了一份电影编辑的工作。工作的环境很糟糕,整天躲在那个幽暗封闭的小房间,像一个单人监狱。即使是白天,阳光照进来,也是那么闷,不透气。有时,他坐在那个房间里对着电脑荧幕,觉得那个荧幕宛如怪物的大方形的嘴,深邃幽暗,仿佛要把他的头吸进去。但他认为懂编辑是导演的必要素质,导演应该懂编剧,要懂作曲,最好也要懂表演,像卓别林一样。他原以为,到目前为止,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通向做导演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地运行着。但始料未及的是,就是这个编辑,使他对电影,包括电影导演的意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对于这个“根本转变”,他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弄明白,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自从他懂得了编辑后,编辑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比如一帧视频的长度的缩短,与另一帧视频对接方式的设定,像“融合”,“叠加”和“消散”,一段配音的选择,等等,都会使原来故事的意义遽然变异,原有的“总体感”会迅速崩溃。换句话说,所谓完美的作品,全是由编辑许许多多的细节的偶然选择凑成的,其中的各种可能性,稍有变化,意味大变。后来他不大爱看电影了,他感到很难再回到没有学电影导演,尤其是没有学电影编辑时的状态了。他很难专心,容易走神,极易被枝节和非常次要的细节分神,更重要的是他不再相信电影的“魅力”了。他觉得所有的电影魅力的后面,全是脆弱的编辑,是一系列勉强的随意的东西支撑着,是一寸一寸一厘一厘的人造的东西,它们会毁于一旦,这是他无法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一句话,他对电影的信仰,在编辑的无限可能性中,彻底动摇了。
这个信仰的快速崩塌,其实源于他的信仰本身的脆弱或天真,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人,当他刚开始着迷于女性的时候,却不合时宜地上了一堂有关少女的人体解剖课。这是一系列课程,大肠小肠,肝,脾,肾——消化系统,包括分泌系统,排便利尿,呼吸系统,肺叶,肺泡,还有神经系统,神经元,神经末梢,生殖系统,阴道,子宫,子宫壁,阴道壁的奇怪而粗糙的机理,等等。那些在显微镜下呈现的另一种奇怪的微观世界,不仅没有丝毫美感,反而令他毛骨悚然,而且问题在于,这个生态系统里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比如排泄系统或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位少女的状态和容貌。虽然这是个常识,但他很难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他不愿意,或是他真的没有这样想过。比如那次他追一个女孩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至今都使他迷惑和失落。那是同班的一位秀美的女生,他瞅准了时机递给她一个纸条,漫长的几天后,那女孩来了,也递给他一个纸条,可就在那时,他听到那女孩放了个屁。女孩表情顿时变得尴尬和紧张,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屁放了就收不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对他而言,臭味飘出之后,他好像比那个女生还觉得尴尬难堪,使他很久都不愿意或不太想再给女孩递纸条了。
前言/序言
窈窕文丛:爱情一息尚存
贾梦玮
“窈窕文丛”,顾名思义,作者都是女性,是女作家,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后九○后的青年女作家。关于女作家,关于女性书写,有“女权主义”的说辞,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但也都可以不管。或者说,“窈窕文丛”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远远不止这些。
我相信,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因此,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窈窕文丛”不仅是女性文学,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因为,那不是“他者”,而是她们“自己”。“窈窕文丛”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如纪米萍、夏肖丹、丁霞、刘晋芳、商小燕、娜娜、云惠、阮依琴、唐小糖、芸溪、静川、梅林、汪薇……还有好多个“我”与“她”,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只有她们才能创造,“她们”身心的千疮百孔,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阅读“窈窕文丛”,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我对于“她”的阅读体验,不是同情、怜惜、悲悯等词汇所能概括的。常常,我觉得我就是“她”,就是“她们”,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这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文学的命运。
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窈窕文丛”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或萎缩,或无能,或逃避,或不忠,或模糊不清、不负责任,或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女人都那样了,男人就没有责任?还有幸福可言?男人都这样了,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异性环境颓败了,无论男女,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免不了的,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我们都是伤心之人。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
但是,“窈窕文丛”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爱情至少一息尚存。“窈窕文丛”的每部作品中,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无法否认。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窈窕文丛”中的那些女性,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
广义上的“爱”和“情”是世界的本源。“窈窕文丛”中的作品,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粝、绝望的人生,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她还说:“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女权主义”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我只知道,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
美貌曰“窈”,美心曰“窕”;美状曰“窈”,善心曰“窕”。“窈窕”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丛书以此命名,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好的“君子”呢?“窈窕文丛”既是给女人的,也是给那些男人的。
给“爱”机会,让“爱”创造。
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电子书更好的学习,精心整理了网络上的各种电子书,有PDF版本的,也有TXT版本的,现有一万多本PDF的,七万多本TXT的,还有精心整理的天涯神贴,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的衔接或者扫码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45OMvYM0Jy-BVuJJmRvtw?pwd=w3m9 提取码: w3m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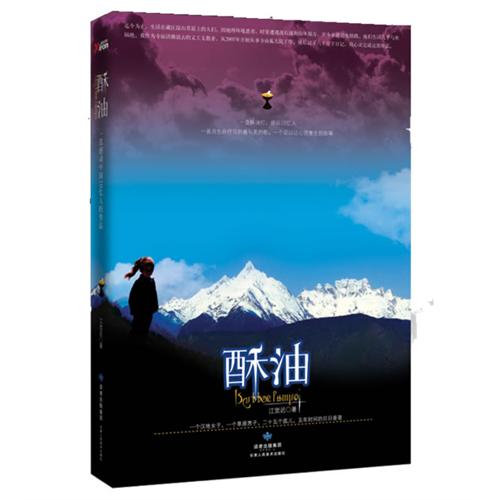


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