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这句让人惊诧的论断出自《批评家之死》中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原型,德国“文学教皇”,大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之口,且是他奉为圭臬的人生座右铭。2002年,马丁·瓦尔泽写出了这部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之死》,讽刺的矛头直指兰尼斯基,没成想却在德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震荡……
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作家汉斯·拉赫不久前为其小说新作被埃尔-柯尼希大加贬损而向批评家当面发出了威胁,因此被认定嫌疑重大而遭逮捕。汉斯·拉赫的朋友,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坚信其无罪,就此展开单方面的调查,先后遭遇各色人物:警察、作家、学者、出版家等等。他与他们逐一交锋和对话,一幅德国当代文坛的写真图景也由此逐渐显现出来。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样貌被不断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语的迷宫,悬念迭生,真相却依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作者简介
马丁·瓦尔泽
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瓦塞堡,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齐名的文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惊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恋爱中的男人》(2008)、《死亡中的男人》(2016)等。他曾于1981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另外也曾获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瓦塞堡,是当代德语文坛中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等齐名的文学大师。主要作品有《惊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恋爱中的男人》(2008)、《死亡中的男人》(2016)等。他曾于1981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另外也曾获黑塞奖、席勒促进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数度在德国引起强烈争议。
精彩书评
瓦尔泽的文字,机智而富有哲理,我深深佩服。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托马斯·曼之后,蕞伟大的德语作家是谁?当然是马丁·瓦尔泽。他是当代的歌德。
——李洱(著名作家)
马丁·瓦尔泽是除德国大主教之外,对德国人影响蕞大的人。他的《迸涌的流泉》和《恋爱中的男人》等作品就体现出他为什么是德国人心灵世界的精确的刻画大师。
——邱华栋(著名作家)
马丁·瓦尔泽这部针砭文坛内幕的讽刺作品写得妙语连珠,逸闻趣事信手拈来……瓦尔泽从未写过如此优秀、如此泼辣的篇章。
——德国《焦点周刊》
瓦尔泽这部小说得益于一种屡试不爽的搭配:犯罪,性,精神病,宗教,政治,无处不在的滑稽描写。统揽一切的,则是失意者的尖刻眼光。
——霍斯特-尤尔根·格里克(德国评论家)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托马斯·曼之后,蕞伟大的德语作家是谁?当然是马丁·瓦尔泽。他是当代的歌德。
——李洱(著名作家)
马丁·瓦尔泽是除德国大主教之外,对德国人影响蕞大的人。他的《迸涌的流泉》和《恋爱中的男人》等作品就体现出他为什么是德国人心灵世界的精确的刻画大师。
——邱华栋(著名作家)
马丁·瓦尔泽这部针砭文坛内幕的讽刺作品写得妙语连珠,逸闻趣事信手拈来……瓦尔泽从未写过如此优秀、如此泼辣的篇章。
——德国《焦点周刊》
瓦尔泽这部小说得益于一种屡试不爽的搭配:犯罪,性,精神病,宗教,政治,无处不在的滑稽描写。统揽一切的,则是失意者的尖刻眼光。
——霍斯特-尤尔根·格里克(德国评论家)
目录
《批评家之死》风波(译者序)
第一部涉案
第二部招供
第三部粉饰乾坤
第一部涉案
第二部招供
第三部粉饰乾坤
精彩书摘
第一部涉案
1.
既然大家并不期望我来撰写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我就必须谈谈我为什么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玫瑰十字会……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的研究领域。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进展的事情,我的确中断了《从苏索到尼采》一书的撰写。我所中断的,与其说是写作本身,不如说是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书的内容:把个性色彩带进德语的,不是让尼采获益匪浅的歌德,而是苏索,埃克哈德,伯麦。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语言造就了我们的体验能力和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读者,看不出神秘主义者与歌德、与歌德之后的尼采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只不过给前者带来快乐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说明,因为我在撰写我的朋友汉斯·拉赫的故事的时候,有可能受我平时写作风格的影响。我们俩,汉斯·拉赫和我,都从事写作。
出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被约斯特·李特曼邀请去看他的收藏。约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手稿,数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间还找不出第二个。我住在安博萨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这里,我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鹿特丹报》——我在阿姆斯特丹总是读这份报纸——的时候得知汉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报上说是谋杀嫌疑。尽管我在国外总把读当地报纸当作一种消遣,我还是赶紧去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他主办的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门诊时间》中抨击了汉斯·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节目结束后,这位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来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击的作家在此对他进行了大肆辱骂。每播放一期《门诊时间》,埃尔-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别墅里搞这么一个聚会,至于说汉斯·拉赫是如何混进去的,这还是个谜。别墅聚会的客人名单上并没有汉斯·拉赫,按照惯例,一个刚刚“轮上”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作家是不会受到邀请的。虽说汉斯·拉赫本人也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书,但依照出版社的规矩,他在那一天没有资格到场。很明显,汉斯·拉赫想立刻对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报以拳脚。据说,在两个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时候,他喊道:忍气吞声的时候过去了。埃尔-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参加晚会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学、媒体、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对于拉赫这句话,他们不啻感到诧异,他们简直深感震惊和厌恶,毕竟谁都知道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父辈中有犹太人,其中几个还是种族大屠杀的牺牲品。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埃尔-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车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别墅前面,汽车的散热器上面扔着他的黄色羊绒套头毛衣,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上总是将这毛衣挽起来搭在双肩。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本人却是无影无踪。那天夜里几乎下了半米深的雪。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于是,第二天汉斯·拉赫有了谋杀嫌疑。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不想回答任何的问题,他很快就被收押。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他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读着上述报道,我呼吸都有点困难。但我知道这不是汉斯·拉赫干的。如果你用心观察过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直觉。虽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读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马上给约斯特·李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得马上回慕尼黑。我本想给他解释我必须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发现这话还不好说。我只好对他讲:一个朋友陷入了困境。要想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似乎还得像外国人那样遣词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么东西给没有。我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总台向我要过身份证,我因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来。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有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小伙子把东西送了过来。我没有错过自己选中的那班火车。可是,火车走了一个钟头便停了下来,停在空旷的荷兰大地。我们没得到任何解释。等到几个乘客嚷嚷起来之后,列车广播里才通知说:Dezetreinisafgehaakt(荷兰语:本次列车取消)。我们不得不下来等救援列车。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和汉斯·拉赫、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关系。我需要一个冷静思索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是否可以如此仓促地赶回慕尼黑。我的想法很单纯。可是,当你脑子里开始计算、盘算、掂量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汉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吗?名气很大、几乎成为明星的汉斯·拉赫,和仅仅在专业圈子里游荡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算得上朋友吗?我跟他成为朋友,也许仅仅因为我们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串门?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马尔森大街,就是说,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格恩地区的画家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伯根豪森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汉斯·拉赫这么说过。他显然比我年轻许多,看事情也比我乐观。我们俩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对方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同住格恩区,我们俩成不了朋友。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从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写到一气呵成的时事评论,我则一头扎进群星闪烁的边缘世界,一个由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构成的世界。然而,当我们在韦森东克——这是一位对时事也感兴趣的哲学教授——在格伦瓦尔德的别墅里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在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一声“再见”。我们俩都很吝惜时间。我们称不上什么密友,这也许因为我们处理这种关系非常慎重。而且我比他还慎重。虽说我们在韦森东克的别墅结识不久便直呼对方汉斯、米夏埃尔,但这无非因为我们在国外,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走得比较多。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叫我米夏埃尔了。根据经验,只有那些对我有好感,或者说那些为人真诚的才这么做。汉斯·拉赫具有真诚待人的天赋。这我一下就感觉出来了。我和他都不属于这里的核心圈子,这个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讳。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时我们合打一个出租,车费对半分,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够让对方请客。我们俩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我倒觉得挺好。我们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请的原因。韦森东克向我问了一些有关卡巴拉的问题,因为《南德意志报》向他约稿,要他评论革舜·肖勒姆的一本书。我当然没好承认韦森东克所说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丝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觉。对于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热衷于时事的韦森东克写书评。话又说回来,韦森东克在提问之前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向他约稿,他之所以答应写这篇书评,完全是因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汉斯·拉赫认为,他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法兰克福汇报》对他不太客气,甚至公然骂他是民粹主义者。该报一位社长还亲自上阵。那天晚上韦森东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地试探,看他是否适合进韦森东克圈子。他还说,我一定注意到韦森东克在提到那个发行人的名字时总要加上“法西斯”这一定语。这个骂人的口头禅明显出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初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那些人,现在虽然明显有了老态,但还是不肯割爱。
尽管我——书写划时代历史巨著的人绝不会在闲聊中消耗夜晚的时光——哪儿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报纸,所以我照样知道谁和谁一帮,谁和谁作对。余下的事情西尔伯福克斯教授会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或者在电话上向我通报。正如他自己高高兴兴说的,他和上帝、和人类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电话号码。他高调地赞扬了我那本论述神秘主义的书。他的颂扬既见诸报纸,也耳闻于广播。后来他又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里找我聊了起来。他说有句话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经第四次看见我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我:我们属于同一个票区。一听说我家住格恩,他赶紧提醒我,汉斯·拉赫也住在那里。他接着补充说,他的绰号就归功于汉斯·拉赫。他认为汉斯·拉赫给他起的绰号也可能出现在瓦格纳的《纽伦堡工匠歌手》里面。说到这儿,我只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嗬,他高声惊叹道,真有意思。整个慕尼黑就您一个人不知道。不过我自个儿传播自个儿的绰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接着又说,汉斯·拉赫把他西尔伯福克斯教授称为西尔本福克斯,是因为他一次跟人聊天时把汉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形容为作茧自缚的伟大作品。在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说句什么话,都会搞得路人皆知。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哪儿的文化人也不会跟慕尼黑这帮子似的喜欢流言蜚语。就这样,他在休息厅里对着我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是在他证明他是哈拉兴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热爱格恩之后打开的。对于一个文学教授,格恩就是汉斯·拉赫的同义词。对于那片可爱的小市民住宅区来说,由于响起了入场的铃声,他加快了说话速度,汉斯·拉赫的名气也可以说太大了点。他早该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继续说。从他的音调和微笑可以判断,他的话带有讽刺意味。教授讲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射我没有资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可是我没法不听出这层意思。
世上没有一个警察会认为我有谋杀嫌疑。但是他们会怀疑汉斯·拉赫,尽管他杀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样微乎其微。当我在报纸上阅读有关汉斯·拉赫的报道时,我没有考虑他是否需要我。我无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汉斯·拉赫摆脱这一荒唐的怀疑。我没法想象任何事情。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给人多管闲事的印象。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无非偶然做了他的邻居。平时我很容易脸皮薄。现在我的脸皮却一点不薄。我必须去。马上去。去慕尼黑。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德国最大的监狱之一,1901年落成)。
……
1.
既然大家并不期望我来撰写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我就必须谈谈我为什么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玫瑰十字会……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的研究领域。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进展的事情,我的确中断了《从苏索到尼采》一书的撰写。我所中断的,与其说是写作本身,不如说是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书的内容:把个性色彩带进德语的,不是让尼采获益匪浅的歌德,而是苏索,埃克哈德,伯麦。由于资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语言造就了我们的体验能力和认知能力,所以我们,也就是读者,看不出神秘主义者与歌德、与歌德之后的尼采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只不过给前者带来快乐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说明,因为我在撰写我的朋友汉斯·拉赫的故事的时候,有可能受我平时写作风格的影响。我们俩,汉斯·拉赫和我,都从事写作。
出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被约斯特·李特曼邀请去看他的收藏。约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手稿,数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间还找不出第二个。我住在安博萨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这里,我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鹿特丹报》——我在阿姆斯特丹总是读这份报纸——的时候得知汉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报上说是谋杀嫌疑。尽管我在国外总把读当地报纸当作一种消遣,我还是赶紧去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安德烈·埃尔-柯尼希在他主办的家喻户晓、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门诊时间》中抨击了汉斯·拉赫的新作《没长脚趾甲的女孩》。节目结束后,这位批评家一如既往地来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击的作家在此对他进行了大肆辱骂。每播放一期《门诊时间》,埃尔-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别墅里搞这么一个聚会,至于说汉斯·拉赫是如何混进去的,这还是个谜。别墅聚会的客人名单上并没有汉斯·拉赫,按照惯例,一个刚刚“轮上”埃尔-柯尼希的《门诊时间》的作家是不会受到邀请的。虽说汉斯·拉赫本人也在皮尔格里姆出版社出书,但依照出版社的规矩,他在那一天没有资格到场。很明显,汉斯·拉赫想立刻对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报以拳脚。据说,在两个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时候,他喊道:忍气吞声的时候过去了。埃尔-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参加晚会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学、媒体、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对于拉赫这句话,他们不啻感到诧异,他们简直深感震惊和厌恶,毕竟谁都知道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父辈中有犹太人,其中几个还是种族大屠杀的牺牲品。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埃尔-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车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别墅前面,汽车的散热器上面扔着他的黄色羊绒套头毛衣,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电视上总是将这毛衣挽起来搭在双肩。安德烈·埃尔-柯尼希本人却是无影无踪。那天夜里几乎下了半米深的雪。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于是,第二天汉斯·拉赫有了谋杀嫌疑。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不想回答任何的问题,他很快就被收押。根据有关方面的鉴定,他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读着上述报道,我呼吸都有点困难。但我知道这不是汉斯·拉赫干的。如果你用心观察过一个人,你就会有这种直觉。虽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读报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
我马上给约斯特·李特曼打电话,告诉他我得马上回慕尼黑。我本想给他解释我必须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发现这话还不好说。我只好对他讲:一个朋友陷入了困境。要想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似乎还得像外国人那样遣词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么东西给没有。我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总台向我要过身份证,我因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来。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很快就有一个亚洲人模样的小伙子把东西送了过来。我没有错过自己选中的那班火车。可是,火车走了一个钟头便停了下来,停在空旷的荷兰大地。我们没得到任何解释。等到几个乘客嚷嚷起来之后,列车广播里才通知说:Dezetreinisafgehaakt(荷兰语:本次列车取消)。我们不得不下来等救援列车。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和汉斯·拉赫、安德烈·埃尔-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关系。我需要一个冷静思索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是否可以如此仓促地赶回慕尼黑。我的想法很单纯。可是,当你脑子里开始计算、盘算、掂量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冒出来了。汉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吗?名气很大、几乎成为明星的汉斯·拉赫,和仅仅在专业圈子里游荡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算得上朋友吗?我跟他成为朋友,也许仅仅因为我们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串门?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马尔森大街,就是说,我们住在风景如画的格恩地区的画家村。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伯根豪森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汉斯·拉赫这么说过。他显然比我年轻许多,看事情也比我乐观。我们俩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对方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同住格恩区,我们俩成不了朋友。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从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写到一气呵成的时事评论,我则一头扎进群星闪烁的边缘世界,一个由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构成的世界。然而,当我们在韦森东克——这是一位对时事也感兴趣的哲学教授——在格伦瓦尔德的别墅里初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理由不在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一声“再见”。我们俩都很吝惜时间。我们称不上什么密友,这也许因为我们处理这种关系非常慎重。而且我比他还慎重。虽说我们在韦森东克的别墅结识不久便直呼对方汉斯、米夏埃尔,但这无非因为我们在国外,尤其是在英美国家走得比较多。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叫我米夏埃尔了。根据经验,只有那些对我有好感,或者说那些为人真诚的才这么做。汉斯·拉赫具有真诚待人的天赋。这我一下就感觉出来了。我和他都不属于这里的核心圈子,这个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讳。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时我们合打一个出租,车费对半分,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或者说不能够让对方请客。我们俩一开始就显得小里小气,我倒觉得挺好。我们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请的原因。韦森东克向我问了一些有关卡巴拉的问题,因为《南德意志报》向他约稿,要他评论革舜·肖勒姆的一本书。我当然没好承认韦森东克所说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丝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觉。对于神秘主义、卡巴拉、炼金术,我可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们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热衷于时事的韦森东克写书评。话又说回来,韦森东克在提问之前也说了,他们之所以向他约稿,他之所以答应写这篇书评,完全是因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汉斯·拉赫认为,他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法兰克福汇报》对他不太客气,甚至公然骂他是民粹主义者。该报一位社长还亲自上阵。那天晚上韦森东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地试探,看他是否适合进韦森东克圈子。他还说,我一定注意到韦森东克在提到那个发行人的名字时总要加上“法西斯”这一定语。这个骂人的口头禅明显出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初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那些人,现在虽然明显有了老态,但还是不肯割爱。
尽管我——书写划时代历史巨著的人绝不会在闲聊中消耗夜晚的时光——哪儿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报纸,所以我照样知道谁和谁一帮,谁和谁作对。余下的事情西尔伯福克斯教授会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或者在电话上向我通报。正如他自己高高兴兴说的,他和上帝、和人类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电话号码。他高调地赞扬了我那本论述神秘主义的书。他的颂扬既见诸报纸,也耳闻于广播。后来他又在室内乐剧院的休息厅里找我聊了起来。他说有句话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经第四次看见我坐在他前面两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时也提醒我:我们属于同一个票区。一听说我家住格恩,他赶紧提醒我,汉斯·拉赫也住在那里。他接着补充说,他的绰号就归功于汉斯·拉赫。他认为汉斯·拉赫给他起的绰号也可能出现在瓦格纳的《纽伦堡工匠歌手》里面。说到这儿,我只好承认我不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嗬,他高声惊叹道,真有意思。整个慕尼黑就您一个人不知道。不过我自个儿传播自个儿的绰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接着又说,汉斯·拉赫把他西尔伯福克斯教授称为西尔本福克斯,是因为他一次跟人聊天时把汉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形容为作茧自缚的伟大作品。在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说句什么话,都会搞得路人皆知。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哪儿的文化人也不会跟慕尼黑这帮子似的喜欢流言蜚语。就这样,他在休息厅里对着我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是在他证明他是哈拉兴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热爱格恩之后打开的。对于一个文学教授,格恩就是汉斯·拉赫的同义词。对于那片可爱的小市民住宅区来说,由于响起了入场的铃声,他加快了说话速度,汉斯·拉赫的名气也可以说太大了点。他早该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继续说。从他的音调和微笑可以判断,他的话带有讽刺意味。教授讲这句话,当然没有影射我没有资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可是我没法不听出这层意思。
世上没有一个警察会认为我有谋杀嫌疑。但是他们会怀疑汉斯·拉赫,尽管他杀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样微乎其微。当我在报纸上阅读有关汉斯·拉赫的报道时,我没有考虑他是否需要我。我无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国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帮助汉斯·拉赫摆脱这一荒唐的怀疑。我没法想象任何事情。我甚至没法想象自己会给人多管闲事的印象。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无非偶然做了他的邻居。平时我很容易脸皮薄。现在我的脸皮却一点不薄。我必须去。马上去。去慕尼黑。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德国最大的监狱之一,1901年落成)。
……
前言/序言
《批评家之死》风波
(译者序)
2002年5月上旬,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君特·贝格当着马丁·瓦尔泽的面,把瓦尔泽的长篇新作《批评家之死》的打印稿交给了《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任胡伯特·施皮格尔,希望按照老规矩办事。这家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首屈一指的德国报纸与瓦尔泽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他有六部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由该报连载。5月28日,报社通知出版社,他们不会刊载《批评家之死》。次日,《法兰克福汇报》文艺部主任弗兰克·席尔马赫发表了致马丁·瓦尔泽的公开信,对《批评家之死》进行重炮轰击。他列举瓦尔泽两条罪状:其一,用文学方式对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实施报复或者说谋杀;其二,具有反犹倾向,因为他不仅“追杀”了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上演了一系列“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社会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瓦尔泽和他尚未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为主题的舆论大战。参战者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电子版)的,也有没见过文本就已忿忿然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几十家传媒为这场舆论战推波助澜。打响第一枪的《法兰克福汇报》自然要冲锋陷阵,对瓦尔泽进行系列批判。其中既有义愤填膺的读者来信,也有冷静老道的分析文章。一位没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写道:“瓦尔泽用如此险恶和残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最优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仇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国的犹太人认为非离开德国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会跟他们一道走。”善于对文学做“外部”研究的批评家马利乌斯·梅勒告诉大家:在《门诊时间》中出现了犹太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和玛莎·弗莱迪)糟蹋德国作家(汉斯·拉赫)并褒扬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局面——他知道玛莎·弗莱迪的原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是犹太作家。与《法兰克福汇报》势均力敌的《南德意志报》毫不犹豫地唱起了反调。评论家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对一部尚未问世的作品横加挞伐,可谓闻所未闻;在与瓦尔泽和莱希-兰尼斯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学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看来,《批评家之死》“没有反犹倾向,但是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伊尔瑟·艾辛格悲叹瓦尔泽已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此同时,诸多地方报纸和另外几家赫赫有名的报刊——如《新苏黎世报》和《法兰克福评论》,如《时代周报》和《焦点周刊》——也都做了相关的评论和报道,网上论坛也非常热闹。急剧升温的争论甚至让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社民党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认为,《批评家之死》紧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后出现,自然“极具挑衅意味”,基民党秘书长劳伦茨·迈耶则呼吁文艺界人士在讨论反犹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遣词造句,以免造成误解”。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前后矛盾的报道。一会传说瓦尔泽学生时代的女友、具有犹太血统并且被视为反犹问题专家的露特·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不是反犹小说,一会又有报道说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的确具有反犹倾向;《法兰克福汇报》一度报道,瓦尔泽的小说使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深受伤害,几天之后又被迫进行更正,因为凯尔泰斯说的是“瓦尔泽深受伤害”。面对这等形势,苏尔坎普出版社也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人反对出版该书,其中包括莱希-兰尼斯基和哈贝马斯这类重量级人物:前者说瓦尔泽“还没有写过这么次的小说”,后者声称,如果这样一本触犯了道德底线的小说得以出版,他将退出苏尔坎普出版社基金会(哈贝马斯后来的确退出了基金会,但不是因为瓦尔泽,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上要求出版《批评家之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网上盗版日益猖獗(出版社为此发出了起诉侵权的威胁)。6月5日,出版社终于拍板,决定将原定8月出版的《批评家之死》提前出版。6月26日,《批评家之死》终于在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烟草大亨的儿子)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包括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格拉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说《批评家之死》是“影射小说”,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埃尔-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莱希-兰尼斯基的漫画像,不管人们对这幅漫画有何道德或者艺术评判;说到“反犹小说”,读者多半要皱起眉头,因为席尔马赫所控诉的“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惟有透过席尔马赫的有色眼镜才能看到:用希特勒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这句话让无数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来恐吓具有犹太血统的批评家,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评家发音不标准,实际是在讽刺意第绪语(历史上生活在中、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内部交流语言);“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埃尔-柯尼希夫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在影射因为辱骂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里姆茨玛则认为瓦尔泽在戏仿托马斯·曼针对犹太学者特奥多·莱辛被纳粹特务刺杀一事所做的恶毒评论:“这么死符合他的形象”);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常见的反犹笔法,等等。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便是认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从未将埃尔-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据统计,埃尔-柯尼希的“突出”特征有69个,其中能够与他悬而未决的犹太人身份勉强挂钩或者说能够解释为反犹滥调的仅占10%到15%),反犹滥调反倒有可能从席尔马赫的牵强附会中诞生。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起码的文本支持,他的动机也受到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便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批评家之死》风波不是什么游戏,因为当事各方都当了真、都动了情、都挂了彩。瓦尔泽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讦,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甚至公开表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瓦尔泽,瓦尔泽本人一方面也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恶意损害其名誉的做法,另一方面承认自己“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这本书跟大屠杀扯到一起,想到了就不会写了”。一向威风凛凛的批评霸主莱希-兰尼斯基,第一次在德国文坛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所以他给瓦尔泽定了最为严重的罪名:《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犹太人”(席尔马赫抨击瓦尔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掀起《批评家之死》风波的《法兰克福汇报》,不仅留下“派性”、“狭隘”等恶名(与之合作近二十五年的著名学者迪特·博希迈耶只因在别处发表了一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便遭到无情封杀),而且遭遇了一阵解除订报合同的风潮。赚钱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也算不上赢家:德高望重的出版社老板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他是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原型)在这场风波中去世,出版社随后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与之分道扬镳的有社长和编辑,还有瓦尔泽这样的名作家。
有人说,《批评家之死》风波是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也有人称之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能就此把事情简单地归咎于《法兰克福汇报》的狭隘或者派性(莱希-兰尼斯基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了近30年的文学部主任,他也栽培过席尔马赫)。《批评家之死》之所以引发如此一场文学政治风波,是因为它牵涉到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而且碰上比较敏感的时间。
《批评家之死》的作者是瓦尔泽,它所讽刺的对象是莱希-兰尼斯基。这已形成强强对峙的局面。莱希-兰尼斯基何许人耶?他1920年出生在波兰,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德国念中学,随后作为犹太人被遣送到华沙的犹太隔离区,1943年得以逃脱,随后加入波兰共产党。1958年利用出国之机移居联邦德国,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叱咤风云的文学批评家。如今他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教皇”,是一个堪称超级巨星的批评家,一个让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的奇才。公众喜欢他的文字,更欣赏他的现场或者电视形象。作家们畏惧他的批评,因为他把“颁发死亡证书”视为己任,喜欢将人一棍子打死,但是他们更怕他沉默,因为他的沉默会更加严重地损害他们的新作。与他对垒的瓦尔泽也绝非等闲之辈。瓦尔泽于1927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瓦瑟堡,二战后期服过一年兵役,1946至1951年在图宾根和雷根斯堡攻读文学、哲学、历史,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南德意志电台做过几年记者和导演。1953年加入对联邦德国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47社。他和同岁的格拉斯、和年长10岁的海因里希·伯尔同属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像他们二位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非因为他缺少艺术成就和艺术才华。他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他有创作有理论,既写长篇(多达十几部)也写中短篇,早年还写过剧本。他还撰写了诸多反响甚大,甚至具有轰动效果的政论、随笔、演说辞。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丁·瓦尔泽就等于忙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的汉斯·拉赫加上醉心于高深学术研究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瓦尔泽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他获得的各种奖项有十几个,其中包括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和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功勋奖章。此外,他还享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在有生之年享受过的待遇:雕塑家彼特·林克为瓦尔泽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说《一匹在逃的马》),塑像自1999年6月起便矗立在瓦尔泽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然而,这周身的荣誉勋章并不妨碍瓦尔泽成为争议人物:20世纪70年代他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左派,20世纪80年代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90年代人们议论他是否有逃避历史的倾向。瓦尔泽的名气也未能阻止莱希-兰尼斯基在将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中对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莱希-兰尼斯基对他的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的评论在文学圈内无人不晓:“这是一本无足轻重、糟糕透顶、惨不忍睹的小说。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己为他,我们希望这本书尽快被人忘掉”。当然,莱希-兰尼斯基也不否认瓦尔泽是个天才。他在评论长篇小说《时间过半》(1960)时便感叹说:“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他甚至把瓦尔泽看作“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对于瓦尔泽来说,“文学教皇”既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他自述在1976年9月的一个夜晚梦见莱希-兰尼斯基追着找他谈话,他在1977年写过一篇题为《论教皇们》的文章,1993年又把“教皇”写进了长篇小说《互不相干》。让瓦尔泽感受最深的,是批评家的话语霸权,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绝对话语霸权。他用了一个德国式比喻来表达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就我俩的关系而言,他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其实任何一位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莱希-兰尼斯基先生,就我俩关系而言,我是犹太人。”如果没有对莱希-兰尼斯基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十三年之久的《文学四重奏》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瓦尔泽不可能把埃尔-柯尼希及其《门诊时间》写得如此活灵活现。
批评家得罪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作家恨批评家同样自然(莱希-兰尼斯基更把作家对他的深仇大恨视为荣耀,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便不无快意地讲述了有多少德语作家想要他的命),所以让批评家死去的小说屡见不鲜,公众一般也都处之坦然。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西尼亚克虚构过以法兰西的批评大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贝尔纳·皮沃——为对象的连环杀人案(《费迪南·塞利纳》,1997),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让一个作家把一个批评家推下了地铁站台(《脸在何方》,2002),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也让一个酷似莱希-兰尼斯基的批评家命丧黄泉(《黄色小说》,2002)。并未让批评家死去的《批评家之死》,之所以掀起如此道德狂澜,主要因为触及到犹太人的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民族,德国人也知罪认罪,所以才有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1970年10月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庄严下跪。忏悔历史,杜绝一切反犹倾向,这是联邦德国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原则。反犹行动,反犹言论以及各种勾销或者淡化灭犹罪行的企图,全都受到舆论、法律乃至国家机器的约束(一些地方的犹太教堂门口常见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一方面是根深蒂固、改头换面的反犹思想,另一方面是深刻的忏悔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一形势决定了德国社会有关反犹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譬如,许多德国人对“DerJude”(犹太人)这个词存有心理障碍。他们知道“DerJude”过去是贬义词,他们也知道这个词现在不应该带有贬义,但是他们却因为担心对犹太人不敬而常常避免使用这个词(不说“某某某是犹太人”,只说“某某某出生在犹太家庭”等)。莱希-兰尼斯基就和《法兰克福汇报》的某个负责人讨论过能不能说“DerJudeKafka”(犹太人卡夫卡)。由于那段史无前例的灭犹历史,德国人也闹不清楚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何时才能抬起悔罪的头。萨克森州司法部长、一度被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的斯特凡·海特曼便因为说了一句“我们必须成为普通民族中的普通一员”而让人怀疑他想扔掉德国人的历史包袱。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在能否以及如何批评以色列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德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曾经担任过科学教育部和经济部部长的尤尔根·默勒曼,就因为在和德国犹太人协会副主席弗利德曼的辩论中说了下面两句话而引起舆论哗然:“可惜在德国有反犹分子,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但是我担心,恐怕没有谁比沙龙先生和德国的一位弗利德曼先生——此人尖刻傲慢而且不宽容——招来了更多的反犹分子。这样可不行,我们德国人必须能够做到可以批评沙龙的政策而不必被扣上反犹的帽子”。人们纷纷谴责默勒曼的言论带有“犹太人必有可恶之处”的弦外之音。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已经把足球术语嫁接到频繁而严肃的反犹问题讨论,他们越来越喜欢谈论A牌:A=Antisemitismus(反犹),A牌=给反犹份子准备的黄牌或者红牌。
默勒曼事件出现在2002年5月中旬,距离席尔马赫发难只有两周时间,所以瓦尔泽很快就被比作“文学界的默勒曼”。对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振聋发聩标题的文章——《我们的奥斯威辛》(1965)和《说不尽的奥斯威辛》(1979);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卡夫卡博士论文的第一人;他发现(1989年)并且促成了(1995年)犹太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日记的出版,这些日记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认为应该对瓦尔泽亮A牌的人,多半对他1998年10月11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的演讲耿耿于怀。当时,因为“让德国人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让世界理解了德国”而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答谢致辞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他对“奥斯威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了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wegschauen)——此举违背了“正视”(hinschauen)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质问“无休止地呈现我们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变成了一根“道德大棒”。瓦尔泽还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天后,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同时就瓦尔泽是否想给德国人的悔罪历史划上句号这一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相关争论已汇编成集)。12月12日,瓦尔泽和布比斯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进行对话,两人都认为还需要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谈论大屠杀历史,布比斯也收回了“精神纵火”的说法。12月31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实施修建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犹太裔美国建筑大师、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者彼特·艾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瓦尔泽促使联邦议会做出了这一决定。当时的瓦尔泽对他的祖国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
《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如果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多半会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第二部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反犹问题大讨论与2002年夏天德国舆论界围绕《批评家之死》展开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风波成为虚构的风波的延续。瑞士作家阿道夫·穆什格感叹说:“现实在模仿瓦尔泽的模仿作品。”博希迈耶则联想到王尔德的名言:Literaturealwaysanticipateslife(文学乃生活之母)。可是,人们在佩服瓦尔泽的先见之明的同时不禁要问:瓦尔泽既然深知同胞们谈“犹”色变,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部旨在表达自己“对电视时代文化界的权力运作的体验”的作品里附带一笔敏感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笔给他惹出不少的麻烦,席尔马赫便指责他用“闲来之笔给全书点题”,他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瓦尔泽是有意,还是无意?是考虑不周,还是打算摸摸“politicalcorrectness”(政治正确)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
黄燎宇
2004年5月
2017年修订
(译者序)
2002年5月上旬,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君特·贝格当着马丁·瓦尔泽的面,把瓦尔泽的长篇新作《批评家之死》的打印稿交给了《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任胡伯特·施皮格尔,希望按照老规矩办事。这家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首屈一指的德国报纸与瓦尔泽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他有六部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由该报连载。5月28日,报社通知出版社,他们不会刊载《批评家之死》。次日,《法兰克福汇报》文艺部主任弗兰克·席尔马赫发表了致马丁·瓦尔泽的公开信,对《批评家之死》进行重炮轰击。他列举瓦尔泽两条罪状:其一,用文学方式对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实施报复或者说谋杀;其二,具有反犹倾向,因为他不仅“追杀”了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上演了一系列“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社会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瓦尔泽和他尚未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为主题的舆论大战。参战者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电子版)的,也有没见过文本就已忿忿然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几十家传媒为这场舆论战推波助澜。打响第一枪的《法兰克福汇报》自然要冲锋陷阵,对瓦尔泽进行系列批判。其中既有义愤填膺的读者来信,也有冷静老道的分析文章。一位没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写道:“瓦尔泽用如此险恶和残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最优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仇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国的犹太人认为非离开德国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会跟他们一道走。”善于对文学做“外部”研究的批评家马利乌斯·梅勒告诉大家:在《门诊时间》中出现了犹太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和玛莎·弗莱迪)糟蹋德国作家(汉斯·拉赫)并褒扬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局面——他知道玛莎·弗莱迪的原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是犹太作家。与《法兰克福汇报》势均力敌的《南德意志报》毫不犹豫地唱起了反调。评论家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对一部尚未问世的作品横加挞伐,可谓闻所未闻;在与瓦尔泽和莱希-兰尼斯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学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看来,《批评家之死》“没有反犹倾向,但是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伊尔瑟·艾辛格悲叹瓦尔泽已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此同时,诸多地方报纸和另外几家赫赫有名的报刊——如《新苏黎世报》和《法兰克福评论》,如《时代周报》和《焦点周刊》——也都做了相关的评论和报道,网上论坛也非常热闹。急剧升温的争论甚至让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社民党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认为,《批评家之死》紧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后出现,自然“极具挑衅意味”,基民党秘书长劳伦茨·迈耶则呼吁文艺界人士在讨论反犹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遣词造句,以免造成误解”。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前后矛盾的报道。一会传说瓦尔泽学生时代的女友、具有犹太血统并且被视为反犹问题专家的露特·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不是反犹小说,一会又有报道说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的确具有反犹倾向;《法兰克福汇报》一度报道,瓦尔泽的小说使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深受伤害,几天之后又被迫进行更正,因为凯尔泰斯说的是“瓦尔泽深受伤害”。面对这等形势,苏尔坎普出版社也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人反对出版该书,其中包括莱希-兰尼斯基和哈贝马斯这类重量级人物:前者说瓦尔泽“还没有写过这么次的小说”,后者声称,如果这样一本触犯了道德底线的小说得以出版,他将退出苏尔坎普出版社基金会(哈贝马斯后来的确退出了基金会,但不是因为瓦尔泽,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上要求出版《批评家之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网上盗版日益猖獗(出版社为此发出了起诉侵权的威胁)。6月5日,出版社终于拍板,决定将原定8月出版的《批评家之死》提前出版。6月26日,《批评家之死》终于在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烟草大亨的儿子)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包括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格拉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说《批评家之死》是“影射小说”,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埃尔-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莱希-兰尼斯基的漫画像,不管人们对这幅漫画有何道德或者艺术评判;说到“反犹小说”,读者多半要皱起眉头,因为席尔马赫所控诉的“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惟有透过席尔马赫的有色眼镜才能看到:用希特勒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这句话让无数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来恐吓具有犹太血统的批评家,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评家发音不标准,实际是在讽刺意第绪语(历史上生活在中、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内部交流语言);“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埃尔-柯尼希夫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在影射因为辱骂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里姆茨玛则认为瓦尔泽在戏仿托马斯·曼针对犹太学者特奥多·莱辛被纳粹特务刺杀一事所做的恶毒评论:“这么死符合他的形象”);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常见的反犹笔法,等等。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便是认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从未将埃尔-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据统计,埃尔-柯尼希的“突出”特征有69个,其中能够与他悬而未决的犹太人身份勉强挂钩或者说能够解释为反犹滥调的仅占10%到15%),反犹滥调反倒有可能从席尔马赫的牵强附会中诞生。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起码的文本支持,他的动机也受到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便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批评家之死》风波不是什么游戏,因为当事各方都当了真、都动了情、都挂了彩。瓦尔泽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讦,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甚至公开表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来对付瓦尔泽,瓦尔泽本人一方面也声称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恶意损害其名誉的做法,另一方面承认自己“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这本书跟大屠杀扯到一起,想到了就不会写了”。一向威风凛凛的批评霸主莱希-兰尼斯基,第一次在德国文坛尝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滋味,所以他给瓦尔泽定了最为严重的罪名:《批评家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犹太人”(席尔马赫抨击瓦尔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掀起《批评家之死》风波的《法兰克福汇报》,不仅留下“派性”、“狭隘”等恶名(与之合作近二十五年的著名学者迪特·博希迈耶只因在别处发表了一篇观点相左的文章便遭到无情封杀),而且遭遇了一阵解除订报合同的风潮。赚钱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也算不上赢家:德高望重的出版社老板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他是路德维希·皮尔格里姆的原型)在这场风波中去世,出版社随后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与之分道扬镳的有社长和编辑,还有瓦尔泽这样的名作家。
有人说,《批评家之死》风波是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也有人称之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能就此把事情简单地归咎于《法兰克福汇报》的狭隘或者派性(莱希-兰尼斯基在《法兰克福汇报》担任了近30年的文学部主任,他也栽培过席尔马赫)。《批评家之死》之所以引发如此一场文学政治风波,是因为它牵涉到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话题,而且碰上比较敏感的时间。
《批评家之死》的作者是瓦尔泽,它所讽刺的对象是莱希-兰尼斯基。这已形成强强对峙的局面。莱希-兰尼斯基何许人耶?他1920年出生在波兰,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德国念中学,随后作为犹太人被遣送到华沙的犹太隔离区,1943年得以逃脱,随后加入波兰共产党。1958年利用出国之机移居联邦德国,并在短时间内成为叱咤风云的文学批评家。如今他已是家喻户晓的“文学教皇”,是一个堪称超级巨星的批评家,一个让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的奇才。公众喜欢他的文字,更欣赏他的现场或者电视形象。作家们畏惧他的批评,因为他把“颁发死亡证书”视为己任,喜欢将人一棍子打死,但是他们更怕他沉默,因为他的沉默会更加严重地损害他们的新作。与他对垒的瓦尔泽也绝非等闲之辈。瓦尔泽于1927年出生于博登湖畔瓦瑟堡,二战后期服过一年兵役,1946至1951年在图宾根和雷根斯堡攻读文学、哲学、历史,获博士学位,随后在南德意志电台做过几年记者和导演。1953年加入对联邦德国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47社。他和同岁的格拉斯、和年长10岁的海因里希·伯尔同属战后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像他们二位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非因为他缺少艺术成就和艺术才华。他著述甚丰,涉猎广泛。他有创作有理论,既写长篇(多达十几部)也写中短篇,早年还写过剧本。他还撰写了诸多反响甚大,甚至具有轰动效果的政论、随笔、演说辞。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丁·瓦尔泽就等于忙于五彩斑斓的写作生活的汉斯·拉赫加上醉心于高深学术研究的米夏埃尔·兰多尔夫。瓦尔泽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他获得的各种奖项有十几个,其中包括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和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功勋奖章。此外,他还享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在有生之年享受过的待遇:雕塑家彼特·林克为瓦尔泽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说《一匹在逃的马》),塑像自1999年6月起便矗立在瓦尔泽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然而,这周身的荣誉勋章并不妨碍瓦尔泽成为争议人物:20世纪70年代他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左派,20世纪80年代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20世纪90年代人们议论他是否有逃避历史的倾向。瓦尔泽的名气也未能阻止莱希-兰尼斯基在将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中对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莱希-兰尼斯基对他的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的评论在文学圈内无人不晓:“这是一本无足轻重、糟糕透顶、惨不忍睹的小说。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己为他,我们希望这本书尽快被人忘掉”。当然,莱希-兰尼斯基也不否认瓦尔泽是个天才。他在评论长篇小说《时间过半》(1960)时便感叹说:“也许还从来没有一本写得如此糟糕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他甚至把瓦尔泽看作“他那一代作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对于瓦尔泽来说,“文学教皇”既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他自述在1976年9月的一个夜晚梦见莱希-兰尼斯基追着找他谈话,他在1977年写过一篇题为《论教皇们》的文章,1993年又把“教皇”写进了长篇小说《互不相干》。让瓦尔泽感受最深的,是批评家的话语霸权,特别是电视带来的绝对话语霸权。他用了一个德国式比喻来表达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感觉:“就我俩的关系而言,他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其实任何一位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莱希-兰尼斯基先生,就我俩关系而言,我是犹太人。”如果没有对莱希-兰尼斯基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十三年之久的《文学四重奏》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瓦尔泽不可能把埃尔-柯尼希及其《门诊时间》写得如此活灵活现。
批评家得罪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作家恨批评家同样自然(莱希-兰尼斯基更把作家对他的深仇大恨视为荣耀,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便不无快意地讲述了有多少德语作家想要他的命),所以让批评家死去的小说屡见不鲜,公众一般也都处之坦然。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西尼亚克虚构过以法兰西的批评大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贝尔纳·皮沃——为对象的连环杀人案(《费迪南·塞利纳》,1997),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让一个作家把一个批评家推下了地铁站台(《脸在何方》,2002),德国作家博多·基尔希霍夫也让一个酷似莱希-兰尼斯基的批评家命丧黄泉(《黄色小说》,2002)。并未让批评家死去的《批评家之死》,之所以掀起如此道德狂澜,主要因为触及到犹太人的问题。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民族,德国人也知罪认罪,所以才有联邦总理威利·勃兰特1970年10月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庄严下跪。忏悔历史,杜绝一切反犹倾向,这是联邦德国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原则。反犹行动,反犹言论以及各种勾销或者淡化灭犹罪行的企图,全都受到舆论、法律乃至国家机器的约束(一些地方的犹太教堂门口常见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一方面是根深蒂固、改头换面的反犹思想,另一方面是深刻的忏悔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这一形势决定了德国社会有关反犹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譬如,许多德国人对“DerJude”(犹太人)这个词存有心理障碍。他们知道“DerJude”过去是贬义词,他们也知道这个词现在不应该带有贬义,但是他们却因为担心对犹太人不敬而常常避免使用这个词(不说“某某某是犹太人”,只说“某某某出生在犹太家庭”等)。莱希-兰尼斯基就和《法兰克福汇报》的某个负责人讨论过能不能说“DerJudeKafka”(犹太人卡夫卡)。由于那段史无前例的灭犹历史,德国人也闹不清楚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何时才能抬起悔罪的头。萨克森州司法部长、一度被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的斯特凡·海特曼便因为说了一句“我们必须成为普通民族中的普通一员”而让人怀疑他想扔掉德国人的历史包袱。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在能否以及如何批评以色列这个问题上感到困惑。德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曾经担任过科学教育部和经济部部长的尤尔根·默勒曼,就因为在和德国犹太人协会副主席弗利德曼的辩论中说了下面两句话而引起舆论哗然:“可惜在德国有反犹分子,我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但是我担心,恐怕没有谁比沙龙先生和德国的一位弗利德曼先生——此人尖刻傲慢而且不宽容——招来了更多的反犹分子。这样可不行,我们德国人必须能够做到可以批评沙龙的政策而不必被扣上反犹的帽子”。人们纷纷谴责默勒曼的言论带有“犹太人必有可恶之处”的弦外之音。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人已经把足球术语嫁接到频繁而严肃的反犹问题讨论,他们越来越喜欢谈论A牌:A=Antisemitismus(反犹),A牌=给反犹份子准备的黄牌或者红牌。
默勒曼事件出现在2002年5月中旬,距离席尔马赫发难只有两周时间,所以瓦尔泽很快就被比作“文学界的默勒曼”。对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振聋发聩标题的文章——《我们的奥斯威辛》(1965)和《说不尽的奥斯威辛》(1979);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卡夫卡博士论文的第一人;他发现(1989年)并且促成了(1995年)犹太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日记的出版,这些日记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认为应该对瓦尔泽亮A牌的人,多半对他1998年10月11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的演讲耿耿于怀。当时,因为“让德国人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让世界理解了德国”而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答谢致辞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他对“奥斯威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了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wegschauen)——此举违背了“正视”(hinschauen)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质问“无休止地呈现我们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变成了一根“道德大棒”。瓦尔泽还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天后,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同时就瓦尔泽是否想给德国人的悔罪历史划上句号这一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相关争论已汇编成集)。12月12日,瓦尔泽和布比斯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进行对话,两人都认为还需要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谈论大屠杀历史,布比斯也收回了“精神纵火”的说法。12月31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实施修建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犹太裔美国建筑大师、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者彼特·艾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瓦尔泽促使联邦议会做出了这一决定。当时的瓦尔泽对他的祖国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
《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如果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多半会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第二部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反犹问题大讨论与2002年夏天德国舆论界围绕《批评家之死》展开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风波成为虚构的风波的延续。瑞士作家阿道夫·穆什格感叹说:“现实在模仿瓦尔泽的模仿作品。”博希迈耶则联想到王尔德的名言:Literaturealwaysanticipateslife(文学乃生活之母)。可是,人们在佩服瓦尔泽的先见之明的同时不禁要问:瓦尔泽既然深知同胞们谈“犹”色变,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部旨在表达自己“对电视时代文化界的权力运作的体验”的作品里附带一笔敏感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笔给他惹出不少的麻烦,席尔马赫便指责他用“闲来之笔给全书点题”,他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瓦尔泽是有意,还是无意?是考虑不周,还是打算摸摸“politicalcorrectness”(政治正确)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
黄燎宇
2004年5月
2017年修订
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电子书更好的学习,精心整理了网络上的各种电子书,有PDF版本的,也有TXT版本的,现有一万多本PDF的,七万多本TXT的,还有精心整理的天涯神贴,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的衔接或者扫码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45OMvYM0Jy-BVuJJmRvtw?pwd=w3m9 提取码: w3m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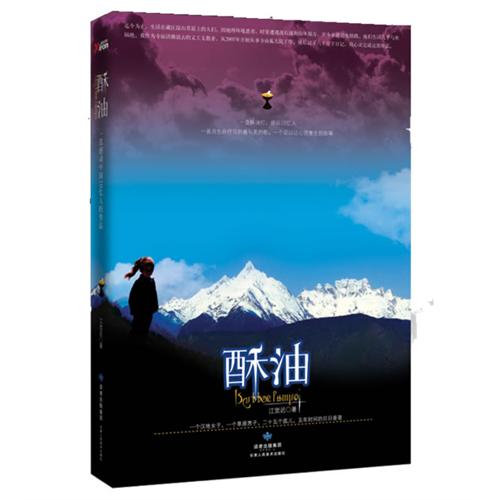


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