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病人》作者、布克奖得主迈克尔?翁达杰具力量的小说
关于战争,关于爱,关于亲情,关于身份,关于未知的敌人,也关于对尘封过往的探索
人气作家、《夜航西飞》译者陶立夏倾情翻译
《安尼尔的鬼魂》是翁达杰一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
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
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水手”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
安尼尔必须背负自己、塞拉斯、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为佛像点睛的安南达深藏的秘密与悲恸。
翁达杰怀揣着对故土悲剧的隐秘伤痛,花费多年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甚至涉猎了书中相关的考古、法医学的研究,让小说叙事达到精湛的完美和准确。作家延续了他的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在对主人公的记忆和运命的层层揭露中,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
作者简介
迈克尔·翁达杰,加拿大小说家、诗人。他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十一岁时随母亲移居英国,十九岁移居加拿大,加入加拿大国籍。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皇后大学,曾长期在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
自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迈克尔·翁达杰已经出版六部长篇小说、童年回忆录《世代相传》、多部诗集、剧本、文学评论集。他也积极参与加拿大独立出版社马车房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工作。他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小说《英国病人》荣获布克奖,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二〇〇〇年出版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获加拿大吉勒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法国美第奇奖、《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小说《遥望》又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迈克尔·翁达杰和同为作家的妻子琳达·斯伯丁住在多伦多。
精彩书评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吉尔奖、美第奇奖获奖作品
翁达杰的非凡成就在于,他似有魔法般地让故国的血腥栩栩如生……正如他在《英国病人》中展示的那样,翁达杰先生能以激烈而出人意料的方式将苦痛与诱惑揉合。
——《纽约时报》
在翁达杰的作品里,可以预见的边界都是可疑的:诗歌,抑或散文?事实,还是虚构?真实,想象?他在记忆、历史、梦境和想象交汇之处写作。
——《纽约书评》
在《安尼尔的鬼魂》中,翁达杰的视角惊人的地方在于那可怕的孤绝:没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置身于集体中,所有的人都被描述成或全然、或彻底的孤身一人,对他们的同伴封闭自身,不管他们如何试图冲破相互之间的障碍。甚至,很多时候,他们都沉迷于这种障碍本身。
——《卫报》
甚至在他揭开真相时,翁达杰仍欲说还休;他通过主人公们孤注一掷且充满激情的行为呈现他们的动机;更重要的,借由那些蚀刻在优美风景和残暴人性的背景中的个体故事,他呈现了一个人、一个国家及其历史的本质。
——《出版人周刊》
目录
作者题记 001
塞拉斯 003
密林里的修行者 067
兄弟 099
安南达 139
老鼠 181
心跳之间 203
命运之轮 235
在远方 263
致谢 273
无明最苦(代译后记) 276
精彩书摘
安尼尔
她划一根火柴,举向暗中,光亮聚拢来,顺着她的手臂蜿蜒而上。她刚看见左手腕上的辟邪棉绳,火柴随即熄灭。自从在朋友的一次法会戴上这守护结之后,没到一个月玫红色就已褪尽。当她在实验室戴上乳胶手套,绳子的颜色就在手套下变得更显浅淡,仿佛凝在冰中。
身边的塞拉斯打开了手电筒,那是他就着火柴的光亮找到的,然后两人在抖动的光晕中前行,向一面金属墙走去。走到墙边后,塞拉斯用手掌大力拍击,他们听到墙后的房间里传来动静声响。“像老婆回来时,男人和女人匆忙下床的声音。”她低声说着,旋即住了嘴。安尼尔和塞拉斯还没有熟稔到可以拿夫妻关系开玩笑。她本想再加一句:亲爱的,我回来了。
亲爱的,我回来了,当她蹲在尸体身边判断死亡时间时,她会这样说。语调有时讥讽有时温柔,视她情绪而定。绝大多数时候,她会在伸手停留在距离尸体肌肤一厘米处探知体温时,这样悄声细语。尸体。不再是他或者她。
“再敲一次。”她要求道。
塞拉斯
他总是遭遇各式各样的死亡。他的工作让他感觉自己是速朽的肉身与不朽的岩画间某种牵绊关连;或许,更奇妙地,维系着信念与意念的不朽。所以一尊六世纪时代的睿智头像被搬走,或者一条辛苦举了数个世纪的手臂突然垂落,都关乎人类的命运。他曾怀抱拥有两千年历史的雕像。也曾将手放置在雕刻成人形的古老而温暖的岩石上。岩石映衬着自己黝黑的肤色,这景象让他获得慰藉。这是他的欢愉之源。毋需来自他人或权贵的说教,而只要将手放置在岩石雕刻成的佛像上,这是拥有生命的岩像,体温随时辰变化,纤毫毕现的面容因雨水或骤然降临的暮色而更改。
岩像的手或许就是他妻子的手。它有相似的肤色和陈旧感,以及熟悉的温柔。凭借她留在房间里的细枝末节,他可以轻易还原她的人生,他们共度的时光。两枝铅笔和一条披肩已足够他勾勒并回忆起她的世界。但他俩的生活却依旧深埋土下。
他曾在黑暗中诉说,却假装尚余一线光亮。但此刻,在这个下午,他带着扑朔迷离的真相重回错综复杂的公众视线。他的举止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知道自己不会被原谅。
迦米尼
他喜欢与陌生人推心置腹,言语幽默。噢,他清楚这一切属于病态——但他并不反感,不反感彼此间的生疏与隐姓埋名的乐趣。
他曾温柔、拘谨但合群。在北方偏远地区的医院工作三年多之后,他将变得更为偏执。一年后,他的婚姻稍纵即逝,此后他几乎都是孤身一人。手术时他只需要一个助手。其他人可以远远站着观看学习。他从不解释自己做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些什么。从不是位好老师,但却是最好的示范者。
帕利帕纳
他走向荒野中每一根梁柱,在一旁站定后紧紧拥住,仿佛它们是旧时故知。他耗费人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岩石和碑文中探寻历史。直到最近几年他才发现了被掩盖的历史,那些被蓄意隐瞒的章节,颠覆了他早年的世界观与知识架构。无论是为掩饰还是为揭露,真相都需仰仗谎言。
他在闪电的光亮中解读那些浅浅的刻痕,在大雨和雷声中将其一一书写。就着一盏便携矿灯或是洞穴中以荆棘生起的火。孤身进行田间考察时,研读那些发生在古老而隐晦的字句背后的对话,在正史与野史之间反复思量,那时候他连续数周不和任何人交谈,于是这些就成为他唯一的言语——一位碑刻家研究四世纪时期某种特有的凿刻方式,却偶遇一个禁忌的故事,它遭到国王、政府和僧侣的查禁,只能隐身字里行间。这些诗句蕴藏着更为黑暗的证据。
迦米尼
他喜欢与陌生人推心置腹,言语幽默。噢,他清楚这一切属于病态——但他并不反感,不反感彼此间的生疏与隐姓埋名的乐趣。
他曾温柔、拘谨但合群。在北方偏远地区的医院工作三年多之后,他将变得更为偏执。一年后,他的婚姻稍纵即逝,此后他几乎都是孤身一人。手术时他只需要一个助手。其他人可以远远站着观看学习。他从不解释自己做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些什么。从不是位好老师,但却是最好的示范者。
他只爱过一个女人,娶的却不是她。后来在波隆纳鲁沃附近的后勤医院,另一个女人让动心,她已是别人的妻子。最终他感觉自己置身恶魔船,而他是船上唯一头脑清醒、神志正常的人。战争年代让他如鱼得水。
帕利帕纳
他走向荒野中每一根梁柱,在一旁站定后紧紧拥住,仿佛它们是旧时故知。他耗费人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岩石和碑文中探寻历史。直到最近几年他才发现了被掩盖的历史,那些被蓄意隐瞒的章节,颠覆了他早年的世界观与知识架构。无论是为掩饰还是为揭露,真相都需仰仗谎言。
他在闪电的光亮中解读那些浅浅的刻痕,在大雨和雷声中将其一一书写。就着一盏便携矿灯或是洞穴中以荆棘生起的火。孤身进行田间考察时,研读那些发生在古老而隐晦的字句背后的对话,在正史与野史之间反复思量,那时候他连续数周不和任何人交谈,于是这些就成为他唯一的言语——一位碑刻家研究四世纪时期某种特有的凿刻方式,却偶遇一个禁忌的故事,它遭到国王、政府和僧侣的查禁,只能隐身字里行间。这些诗句蕴藏着更为黑暗的证据。
安南达
经过她工作台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身后,确保不会碰乱任何东西,然后俯下身,透过他厚厚的镜片看着她的游标卡尺和记重表,仿佛置身寂静的博物馆。他俯得更低,闻着那些器材。科学家的头脑,她想。昨天她留意到他的手指纤细修长,因工作而染成了赭红色。
这时安南达抬起骸骨,拥它入怀。
他的举动却丝毫没有惊吓到她。当埋首于调查研究,因错综复杂的数据耗费数小时心神之后,她也很想伸出手去,将“水手”拥入怀中,只为提醒自己他与她并无不同。他不仅仅是证据,还是神采奕奕却也不乏缺点的凡人,家庭的一员,当他生活的村庄政局突变,在最后一刻他举起了双手,导致手臂折断。安南达抱着“水手”缓步而行,随即又将他放回工作台上,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安尼尔。她微微点头,表示她并不生气。她慢慢站起身来向他走去。一片黄色的细小树叶飘落,滑进骨骸的胸腔,如心脏颤动。
……
前言/序言
作者题记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斯里兰卡陷入动乱,动乱主要涉及三大阵营:政府,南方的反政府叛军以及北方的分裂派武装。叛乱分子与分裂武装同时向政府宣战。最终,作为回应,合法与非法的政府军队被派遣至全国各地,剿灭叛乱分子与分裂派武装。
《安尼尔的鬼魂》是发生在这一政治局势以及历史时期的虚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和灾难事件都属虚构,但确实存在与书中机构类似的组织,类似的事件也曾上演。
今日,斯里兰卡的战争仍在以另一种方式上演。
M.翁达杰
无明最苦(代译后记)
陶立夏
如果遇到翁达杰,我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会是:为什么你的故事里这么多的离散。他曾在《英国病人》中这样写:The sea of night sky hawks in rows until they are released at dusk arcing towards the last colour of the desert. A unison of performance like a handful of thrown seed.
“夜色似海,列队以待的猎鹰在暮色降临时分获得自由,疾速射向荒漠中最后的光亮。如一把种子,整齐划一,脱掌而去。”每每回想他故事里的众多人物,就记起这句话。他们留下很多离去的背影给我这个读者,这些远离故土的浪子们,如一把种子迎风飞扬。
但《安尼尔的鬼魂》是不同的。Honey I’m home.当法医安尼尔跪在受害人身边,这样轻声说的时候,我好像终于找到等了多年、好几本书的那句话。
在这么多离去之后,终于有人归返。Honey I’m home.
从西方整饬的虚无踏进故土染着血色的混沌。安尼尔要放弃自由,重新学会如何对待暴力、对待信仰、对待苦难、对待隔阂。我想这就是《安尼尔的鬼魂》与翁达杰的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
和很多中国读者一样,我因为《英国病人》知晓并爱上了翁达杰。他曾被誉为“无国界作家”的代表人物,从隆美尔的埃及战场到奥尔良的爵士酒吧,从意大利乡间的教堂到安大略湖底的隧道:国家疆界只是地图上的标示而已。关于故土斯里兰卡,翁达杰则在两部作品中重点提及——如果说少年往事萦怀的《猫桌》是皎洁的月球表面,满布名字优美的月海,那么《安尼尔的鬼魂》是沉沉不可示人的月球背面,满是冰冷的死火山和陨石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斯里兰卡爆发内战。毫无解释的逮捕与秘密审讯,不计其数的失踪与死亡,让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无见底的黑暗笼罩着这个国度。佛教中说:无明最苦。
最终,因内战引发的人口失踪问题使斯里兰卡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主人公安尼尔受大赦国际委托前往斯里兰卡调查在考古遗迹中发现的“古尸”的身份。安尼尔之所以获得这个工作多少与其身世有关:她是斯里兰卡裔,在美国求学成长,从事法医鉴证。她从检验第一具尸骸起,就找到了与官方说法相悖的证据:这些尸体并不古老,死亡时间在近年,考古保护区只是为掩盖真相而精心挑选的抛尸地点。她将这具尸骸命名为“水手”,它是大批无名尸骸中的一具,也是她解开谜题的钥匙。
这个名字将为所有受难者命名。
翁达杰的书里最迷人的人物往往是离经叛道的叛逆浪子。除了去国度多年、行事果敢的安尼尔,书中其他两位重要人物塞拉斯与迦米尼也是同样。他们出自翁达杰笔下,当然有与其他作品中的男性角色相同之处,比如对世俗规章的不屑一顾,至于塞拉斯的恩师帕利帕纳,他就像翁达杰最为人所知的角色艾尔马西一样,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他的故事在本书里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短篇存在,一个典型的翁达杰式的隐士:对权威和制度抱有嘲讽的态度,觉得它们无聊且荒唐,对世界有更细微透彻的感知,智慧超群,掌握看似无用却精深的学识。
但他们也有不同以往书中角色的特质,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承担。男主人公塞拉斯似乎是个更符合“儒”的人物,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考古学家,有人脉关系,知晓官场机巧,却愿意为了带着偏见与优越感回国的安尼尔铤而走险不惜生命代价。他的弟弟,外科医生迦米尼则近乎“道”,失去妻子之后以急诊室为家,人为的恶果一次次送到他面前,让他处在崩溃的边缘,但他依旧依靠药物支撑在地狱般的急诊室里缝合伤口,因为如果他放弃,他的兄弟姐妹将承受更多痛苦。甚至是隐居密林并逐渐失明的帕利帕纳,依旧孜孜不倦地照顾着自己在内战中失去双亲的侄女,并将关于斯里兰卡古文字的知识传授于她。
游离的浪子们,在这本书里伸出手来,触碰这个世界。
他们都因心存良知而担负道义,并愿意为信仰殉道。他们的信仰,就是为“鬼魂”守灵:那些无辜惨死无处伸冤的鬼魂 ,那些痛失至亲至爱而在人世踯躅的鬼魂。这也是书名的来历:Anil’s Ghost,我最终选择直译为《安尼尔的鬼魂》。骸骨“水手”代表的那些无法安息的鬼魂,是安尼尔要担负的责任,是她的鬼魂。她将在塞拉斯的帮助下,为他们查明死因,确认身份,获得真正的安息。
简单来看,这是一个“正名”的故事:在斯里兰卡内战中遇害的无名氏们因为身份不明而成为无法安息的孤魂野鬼,安尼尔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查明他们的身份,揭开内战中当权者与反对派犯下的血腥罪恶。
“名”在各种宗教中都是重要的概念。《道德经》的开篇就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圣经》中上帝让亚当为飞禽走兽命名。阴阳术相信,说中即是解脱,施咒与解咒的关键就在一个“名”。无名则无明。
中国的神话故事和这个故事的内涵也有奇妙的关联。仓颉造字,鬼魂哀哭于野:万物将拥有自己的名字,人将从此走出混沌,它们再无晦暗之处可以藏身。
书中人名字的翻译,也像是一个“正名”的过程。
安尼尔,Anil,一个她费尽波折从哥哥那里买来的名字,原本专属于男性。在女主角看来它带着男性的潇洒,读音和形状都有简洁流畅的魅力,是她挣脱女性桎梏的出口,她的第一场反抗,也是她漫长而艰难的觉醒的开端。后来她将离开故土,经历痛苦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爱情,受疾病摧残的友谊,并积累起足够的阅历、学识和勇气来解答最开始的问题:你是谁,来自哪里。为着女主人公最初选择这个名字的理由,我选择用笔画最简单的文字音译“安尼尔”这个名字。
安南达,Ananda,在佛教典籍中译作阿难,是悉达多的堂弟。我选择这个更世俗化的翻译首要考虑是与全书的时代感统一,另一个更潜在的原因是这个人物一直沉浸在无明的苦痛之中,要到最后才因为男主角塞拉斯无言和无条件的守护与支撑才走出泥沼,如果一开始就叫他阿难,似乎太早了。
翻译也可以看作是为一种文字找到另一个名字吧。这绝对不是轻易的差使。翁达杰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再加上他在东西方文化下成长的独特身世,使他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翁达杰文字里有太多东方式的幽微含蓄,但本质精准犀利,这些是他的魅力,也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要尽善尽美地翻译翁达杰,大概需要一双会画工笔的手,轻、巧、稳、准,通识布局之后,层层渲染,我常常觉得力有不逮。
翁达杰对英语的简洁与直接的特性同样熟稔,比如他对这个词的使用:citizened。
寄生在彼此的黑暗中的四个人,我们观众以上帝视角看他们如何冲破个体误解与文化藩篱成为彼此的依靠。当安尼尔跪在安南达的鲜血中,citizened by their friendship——她这样形容安南达和塞拉斯给她的感觉,这个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归属感,还有为人的理性,在屠杀事件与不义之战频发的国度,这个词如同修罗场中的庙宇。在那一刻安尼尔终于明白:安南达——她眼中一无是处的酒鬼;还有塞拉斯——在她看来人浮于事、官僚作派的考古学家,却原来是这块多难的土地上珍贵的“为人”的标准,是她和这个世界之间的纽带。
因为《英国病人》而折服于翁达杰文笔的魅力,这本书让我对他的敬重与喜爱更进一步。我想,这对于翁达杰来说,也是一本意义不同于其他的作品。
安尼尔对斯里兰卡的复杂情绪,几乎是翁达杰的自白。自十一岁那年随母亲离开斯里兰卡,直到二十多年后翁达杰才重新踏上故土。这本书里的世界是他用自己的回忆想象建立起来的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这城池的坚固来自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更脱胎于他对笔下人物的爱和对故土命运的关怀。翁达杰将自己对暴政的愤怒控诉藏在了哀而不伤的笔调下面,他标志性的诗意之下,血色尽染。我用了大半年时间准备,阅读资料,去斯里兰卡探访书中提及的地方,观看岩画与石刻文字。对斯里兰卡这个国度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再来回通读全文,尽管对这个故事早已熟稔,但半年多时间的翻译过程中依旧时常对翁达杰的叙事方式和文字的处理有惊艳之感。
写尽远走的背影的翁达杰,在这本书里终于开始写回归,写伸手的触碰。翁达杰的故事里,曾有很多独自坐在暗中的人。在《安尼尔的鬼魂》里,他们不再独自摸索,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做着保护的手势,这份关怀虽藏在暗中,却最终让历尽苦难的人看见了光亮。当你最终看清它的存在时,一定像我一样感动。
在书的结尾,当安南达穿着塞拉斯的衬衫登上竹梯为佛像开光,塞拉斯以他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使命,遵守了他从未明说的誓言:塑一个代表千万死者的面目,来帮助生者重新找回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塞拉斯这样一个忍辱负重胸怀宽广的兄长,也是翁达杰能给斯里兰卡,他多难而美丽的故土,他善良而坚韧的同胞,最郑重的祝福。
翁达杰用书写的方式告诉我,对我们深爱的那些事物,仅仅观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伸出手去,无比郑重地触碰,感受它的苦痛并给予支撑。
这是一篇译者手记,编辑说我可以写一些比较个人的感受。我想对翁达杰说:如果有什么人曾教化过我冥顽不灵的灵魂,抚慰过我平静外表下的暴戾与躁动,那大概只有你。
还有,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爱有很多种,你的细致与克制,这正是我要读到的。
感谢编辑彭伦给我这个机会翻译翁达杰,也感谢责任编辑索马里的悉心编辑。如果有什么事比相逢更幸福,那就是了解。
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电子书更好的学习,精心整理了网络上的各种电子书,有PDF版本的,也有TXT版本的,现有一万多本PDF的,七万多本TXT的,还有精心整理的天涯神贴,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的衔接或者扫码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45OMvYM0Jy-BVuJJmRvtw?pwd=w3m9 提取码: w3m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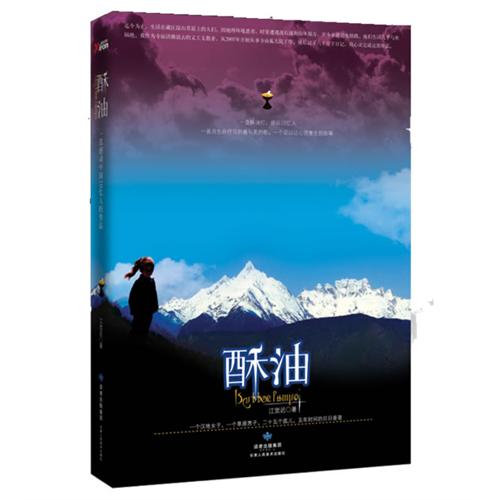


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