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部从心理医生的视角探测世界的小说。海归心理学博士杨博奇,为了从“内部”理解人的秘密,回国后在北京以心理医生为业。一夜暴富的老板金兆山、蝇营狗苟的公务员王颐、为不会说黄段子而苦恼的白领胡大乐、最终选择出家的“爱因斯坦+林徽因”奇女子苒苒……“病人们”一一登场,他们与杨博奇在各不相同的领域——性、婚姻、股市、心理分析、宗教等——反复突进却又无从逾越,在漂浮的都市,他们能否寻找到生活的出口……
作者简介
李陀,生于一九三九年,达斡尔族。评论家,作家,一九八六年,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一九八九年后赴美国访问,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九十年代和陈燕谷共同主编以“新学人、新学术、新思想”为目标的《视界》,并是《今天》的编辑。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参与文学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编辑工作。
精彩书摘
窗玻璃上流淌着一条条水迹。
今天的雨完全是乱下一气,一会儿雨疏风骤,一会儿淅淅沥沥,从早到晚,颠三倒四,喜怒无常。
打开音响,我挑了一张艾拉·菲茨杰拉德的唱碟,让她的歌声缓缓升起——三年前,我花了很多时间挑选、制作了一套CD,几乎把我最喜欢的所有爵士乐,都集在了一起,菲兹杰拉德也在其中。她的声音无论什么时候,都像在朵朵白云之间缓缓流动的阳光,有些耀眼,可是舒服,你闭起眼睛,马上就能感受一种流布全身的暖和。
Now you say you’re lonely
You cried the long night through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Now you say you’re sorry
For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cried, cried a river over you
歌声刚刚升起,手机响了。
是谁?
我不太情愿地拿起手机。
“请问大宝在吗?”
“在——当然在!”
“二宝也在吗?”
“当然也在啊。”
“那我是先和大宝说话,还是和二宝说话?”
这个带着笑意又清凉的声音,一下让我回到半年前一个宁静的黄昏。
那是在九寨沟。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借口和朋友们分了手,终于自己一个人在珍珠滩左近游逛起来。那帮小子一定正在着急,不停地瞎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我给“丢”了。我可不管,尽情享受一个人独行的乐趣。
天色有点暗了,四周寂寂,空无一人,只有红黄相间的秋叶在远山上妩媚,让我一下子想起马松的诗: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
重新回到紧贴着水面,用长长的圆木铺成的小路上,我不慌不忙地领会珍珠滩的美景。
半个钟头前,我在这路上已经走过一次,可是扫兴,同行的这帮人一边吵吵闹闹地嚷着“真美呀!”“好漂亮哦!”一边马不停蹄地往前赶,好像那“真美”不是在他们的脚下,是在前边什么地方——珍珠滩就这样被冲过去了。这等于遇到了一个顶级美人儿,可是匆匆交臂,只能倾慕于一瞥之间,连回头再看一眼都来不及。现在好了,我独自与美人相处,或并肩,或携手,同行同止,相看两不厌。淡淡的暮色里,伴随着清扬的流水声,珍珠滩显得分外婀娜,目力所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到处是流水在浅滩上激起的银色浪花,犹如瞬开瞬谢的千万朵白菊。
太神奇了,眼前一片花海,这海里的每一朵水菊花都霎间即逝,又霎间即生,生生灭灭,无止无休,虚无飘渺,又实实在在。
为什么这种霎间生灭这么吸引人?
我正对着珍珠滩的流水发呆,有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这是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手里提着鞋,赤着足,正站在水波中间,低着头看那些白色的水菊花怎么在她的小腿四周绽放、流逝。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立刻跑过去:“小孩儿!你怎么在水里走?快上来!”
这时候我才看清楚,蹚水的女孩子年纪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小,上身穿蓝白条纹相间的紧身T恤,外边还套了件牛仔小马甲,背着一个米色双肩包,一副太阳镜高高顶在头上,下身是一条牛仔裤,可是裤腿高高地挽起来,修长的腿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在斜阳里闪闪发光。
我的叫声吓了她一跳,但是脸上惊惶的表情很快变成一种蛮横:“谁是小孩儿?你叫什么呀?吓人!”
夕照之下,女孩全身明亮,表情虽然蛮横,可是嗓音里融合着一种很柔和的低音,很好听。
“这是自然保护区,禁止人下水,知道不知道?”
“我刚下来,就洗洗脚,大惊小怪!”
“什么洗洗脚,快上来!”
“你厉害什么呀?我——”
“别废话,快上来。”
“你管得着吗?就不上去,你怎么着?!”
“怎么着?罚款!”
“罚款,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儿的管理人员!你不听劝阻,罚你!”
“不就是罚钱吗?说,罚多少?”
“你这是什么态度?”
“别废话,说,罚多少?”
我和周璎就是这么认识的。
不过,这次的邂逅和争吵,有了一个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先是在餐馆不期而遇,相视一笑,然后凑到一张桌上,一起吃晚饭,再后来,差不多十二点点多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睡到了一张床上。再以后,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验:在连续几个小时汗水淋淋的啪啪啪过程里,每当我想停下来,来一点抒情的时候,周璎总是啪一声拍一下我的屁股说:“别废话!”她还时不时用手拨弄一下我那总是雄赳赳的JJ,然后夸上一句:“真是个好宝贝!”接着又说:“你也是宝贝——一个是大宝贝,一个是二宝贝!”结果,她和大宝贝、二宝贝在第二天都起不了床,不吃不喝,昏天黑地睡了大半天。
一个多星期前,周璎去芝加哥参加一个未来城市绿色发展问题的论坛,通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杳无音信。所以,现在听到了她的声音,我真是高兴。
“这些天过得怎么样?”
“还行吧,活动太多,没什么意思。”
周璎的情绪不太好。
“喂!怎么这么说?你去的地方是芝加哥!那可是蓝调的大本营——”
“是啊,跑了好几处酒吧了。几个乐队都很棒,还和两个黑人喝了酒,一个是钢琴手,一个吹萨克斯,俩人轮流上去演奏,再轮流下来喝酒。”
“你还和人家喝酒!”
“是啊,那感觉,棒极了。”
周璎的声音亮了一点,不再那么黯淡。这是她的一个习惯,情绪不好的时候,嗓音里的一股柔和但是低沉的音色就亮起来,还很好听,反过来,如果心情好,这个声部就低落,好像四重奏中的大提琴飘然下落,孤独地滑向了C弦。最近,好一阵了,她一直这样,即使在嬉笑的时候,我也能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一丝暗影,像一层郁闷的雾气。我本来还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让她换个心情,看来不一定行。
“什么很棒?是人还是音乐?”
“你嫉妒了?告诉你,音乐当然棒,人更棒,你不知道那两个黑哥们儿多棒,多帅。”
我当然嫉妒,可是当然不能承认。
“这有什么可嫉妒的?不就一块儿喝酒嘛。”
“这还差不多。可惜,我明天去纽约,要是九月那时候还在这儿,就能赶上在Grand Park举行的爵士音乐节,那才棒!”
手机已经寂然无声。
可我为什么还一直盯着它?
周璎说她还要在美国待一阵,因为她所在的团队还要走几个城市,考察老美的城市商业网点的规划和布局,然后她还要去洛杉矶看看她的母亲——这可不太寻常。周璎的父母早就离婚了,而且离婚以后两人双双出国,把她放在国内由姥爷抚养,后来周璎母亲又把她接到美国读大学,读博,可是周璎还是和姥爷亲,总是说,什么父母恩?她只有姥爷恩。所以,她和父亲母亲的关系从来不好,平时几乎不怎么来往,偶尔来往还发生冲突,然后周璎会情绪低落,很长时间云浓水暗。
现在她突然要去专门看母亲,怎么回事?
2
窗外依旧雨潺潺。
房间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发闷。
时不时,带着一声爆响,就有一个大雨点砸到水汽蒙蒙的玻璃上,活像一只大飞蛾想到屋子里躲雨,不想撞了个粉身碎骨,爆成一朵透明的水花。
调节一下按钮,我让菲茨杰拉德的歌声重新响起。
灰暗阴沉的房间霎时间明亮了起来。
肯德基外卖来了:十二个香辣鸡翅,再加一杯百事可乐——我的晚饭。为了我酷爱肯德基的香辣鸡翅,周璎好多次批评我粗鄙,说每次请我到餐馆吃饭都后悔,可惜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对她说,这个没办法,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特别的姿势,不论好看难看,那是改不掉的。粗鄙这东西也一样,难改。她对我这些谬论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于和我争论。
刚吃完第五个鸡翅,门铃响了,带着一股幽幽的湿气,我刚放下手里的鸡翅,门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来的是什么人?
打开门,一股寒气迎面扑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来人是个大高个子,西装笔挺,派头十足。奇怪的是,这人身上没一点湿,连贼亮的皮鞋上都没一点水迹,亮亮的鞋头在门口的灯影中闪着银光,很神气。只是客人的脸高高浮在暗影里,模模糊糊,一双眼睛就在这一片模糊中瞪着我,闪闪发亮。
“你是杨博奇?”
“我是,先生找我有事?”
暗影中的眼睛更亮了,能觉得出来,那光芒中有股刺人的怀疑,还有点儿轻蔑。
大概楼道里有个窗子没关上,一阵带着雨意的冷风飒飒吹来。
我板着脸,一声不出。
“你是心理医生?”
到底是他先张了口。
“我是心理医生,这是我诊所。”
我门口旁边的墙上有一块牌子,那牌子是黄铜做的,上边一排是黑体隶书,另一排是花体的英文字,隶书字大,英文字小,内容都一样:杨博奇博士心理诊所。这位大个子客人一定看过这牌子了,但是此刻他又瞥了一眼,好像要鉴定这牌子是不是水货。
我把门一带,用送客的口气说:
“先生到底有没有事?”
我想尽快把这不速之客打发走,回去吃我的鸡翅,不料大个子说:“我先参观参观你这诊所,行吧?”
没等我回答,这家伙已经挤了过来。
他刚向前一跨步,一股冷冷清清的酒气先重重地压到我头上,然后是宽宽的胸膛和肚子。大个子进了房间,先在几平米大小的门厅里站下,迅速地打量了一下,然后也不得到我的允许,就几步走了进来,接待室,咨询室,还差点进了我的卧室——这小子好无礼。
“听说,你这诊所开门不久?”
“对,不久。”
大个子不再说话,拿出一个金灿灿的打火机,啪地打出一个长长的火苗,点燃了手里的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走到我办公桌旁边一个小沙发跟前,一屁股坐下。
“你是在美国念的博士?”
我的回答再简略不过,只有三个字:“不像吗?”
大个子皱了下眉,两眼霎时变成两把闪光的锥子,不过,这就是一刹那,接着是一丝笑容在他脸上漾开,两把锥子也在这几乎看不见的笑里熔化了,一下子无影无踪。他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又吸了口烟,忽然换了种带点亲切的口气说:“我是病急乱投医。”由于带着东北口音,这家伙说起话来语调很硬棒,所以此刻这突如其来的亲切,也还是硬梆梆的,“不瞒你老兄说,我早听说有心理医生这么回事,一直不大信。人家告诉我,心理医生专治心理病,啥是心理病?我想,也就是心病吧?可人的心病也能治?今天路过你这儿,就进来看一看,提着猪头找庙,试试。”
“先生,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如果你需要咨询,需要事先预约。”
“还要预约?”
“对,现在我是下班时间。”
“可我已经来了,例外一下,行吧?”
大个子把身体用力往后一靠,喷了口烟,一串灰蓝的烟圈带着明显的讥讽在空中慢慢飘散。
我没有回答大个子的问题,而是反问过去:“先生,我能不能问一句,你是做什么的?一定是位老板吧?”
从对方的反应里,我知道自己猜对了。果然,大个子笑了,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眯了起来:“行,杨博士,还真有两下。告诉你,我手底下有公司,规模还不能说很大,可也不算小。”
果然是个老板。
“请问贵姓?”
“免贵,我姓金——金兆山。”
“金老板,你进来,说是参观——现在参观完了吧?我这诊所普普通通,没什么可看。”
大个子大概对我的逐客令有点不快,皱着眉看看雨珠四溅的玻璃窗子,没有马上说话。
我真的不耐烦了,得马上赶他走。
我开始想念我的香辣鸡翅,还有七个没吃呢。
为了方便大家利用电子书更好的学习,精心整理了网络上的各种电子书,有PDF版本的,也有TXT版本的,现有一万多本PDF的,七万多本TXT的,还有精心整理的天涯神贴,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的衔接或者扫码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45OMvYM0Jy-BVuJJmRvtw?pwd=w3m9 提取码: w3m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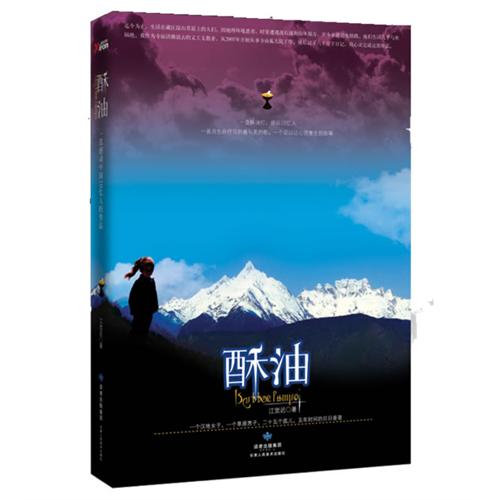


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