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太年轻》《岛上书店》作者加布瑞埃拉·泽文全新杰作!
▶曾经不顾一切,因为太年轻。现在我仍要不顾一切。
▶全美重要媒体联合推荐:《华盛顿邮报》年度小说、《科克斯书评》年度小说
▶《人物》《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周刊》《图书馆周刊》“美国独立书商选书”推荐!
▶《岛上书店》作者加·泽文已 横扫全球30多国。
▶这是一部打破性别与年龄偏见的美丽之作。
这是五个女人的故事,她们处在不同的年纪,因为一个年轻女孩而被牵连在一起,漫长的岁月让她们发展出真正的友善、胆识与决断力。
20岁的阿维娃,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刚进入梦想的行业,就作出了一系列愚蠢的选择,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十多年来,尽管阿维娃选择消失,但关于她的谣言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被牵扯进来的还有13岁的露比、33岁的简、50多岁的艾伯丝,还有64岁的瑞秋。
此刻,她们站在一起,等待那个曾经太年轻的她无所畏惧地回来。
作者介绍
加布瑞埃拉·泽文GabrielleZevin,美国作家、电影剧本编剧。年轻并极富魅力,深爱阅读与创作,为《纽约时报书评》撰稿,现居洛杉矶。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已经出版了八本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14岁时,她写了一封关于“枪与玫瑰乐团”的信函投给当地报社,措辞激烈,意外获得该报的乐评人一职,迈出了成为作家的第一步。一直以来,她对书、书店以及爱书人的未来,充满见解。她的第八本小说《岛上书店》在2014年以史无前例的最高票数,获选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
试读
瑞 秋
1
我的好朋友罗兹·霍洛维茨与她的新任丈夫是通过交友网站相识的。罗兹比我大三岁,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来算不得风韵犹存,因此我也打算试试看——尽管平时我尽量避免上网。罗兹的上一任丈夫患结肠癌去世,而她则开始享受生活了。倒不是说她现任丈夫是什么人中龙凤——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泽西州做汽车玻璃生意——而是说是罗兹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带他到布鲁明黛商场买了几件衬衫,现在他们经常一起到犹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各种兴趣班——西班牙语会话、交际舞、情侣按摩、手工皂制作、蜡烛制作,等等。我倒不急于找个丈夫,因为再结婚会徒增很多麻烦。可我也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再说,能有个人陪我参加兴趣班也不错。我总觉得网络交友是年轻人才玩的东西,可是罗兹说并非如此。“即便如此,”她说,“瑞秋,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啊。”
我问她有哪些建议,她告诉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轻的照片。在网上人人都会撒谎,可讽刺的是,在网上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撒谎。于是我说:“罗兹,亲爱的,真实生活跟这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约见的第一个男人叫哈罗德,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老头。不过哈罗德没有领会我的幽默感,他略带恼火地说:“你没听说过《哈罗德与紫色蜡笔》吗?哈罗德是个小孩啊,瑞秋。”总之,这场约会没了后文。
我约见的第二个男人叫安德鲁,他的指甲很脏,搞得我没心思注意他的人品。点的黄油红糖可丽饼我也吃不下,因为——天啊,他的指甲实在太让人分心了。我真想知道他来赴约之前都干了些什么,是参加园艺竞赛吗?还是把上一个跟他约会的女人埋掉?他说:“瑞秋·夏皮罗,你吃得太少了!”我考虑过把可丽饼打包带走,可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可丽饼不经放,重新加热后就变得黏糊糊、软绵绵的,就算硬着头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经历——因为你会一直想,可丽饼本来多好吃啊!
又过了几个星期,安德鲁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再约会一次,我赶快说:不必了,谢谢你。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斤斤计较,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诉他。或许我对这件事的确有心结,因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干净整齐,可他仍然是个烂人。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谎来唬我。”
我说:“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们的年龄,”我六十四岁,“实在经不起再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说:“告诉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岁。”给了我临别的最后一击。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照片拿给罗兹看了。在我印象里,这张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细回忆后,我想起这是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照的。罗兹说照片上的我的确显得年轻一些,但这样正适合我,不至于年龄悬殊得过分。她说如果我选对了餐厅,再配上合适的灯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我说那跟布兰奇·杜波依斯往台灯上罩围巾有什么两样。后来罗兹在我家阳台上用手机帮我重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约见的第三个男人叫路易斯,他戴着精致的钛合金镜框眼镜,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这不禁让我怀疑自己在选照片这件事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一位美国犹太文学教授,在迈阿密大学任教,他说他以前常跑马拉松,后来髋骨出了毛病,所以现在只跑半程马拉松。他问我平时做不做运动,我说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说到这里——说不定我可以帮他缓解屈肌的病痛?我记得他说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类的话。再后来,为了证明我并不是绣花枕头,我们谈到了读书。我说我非常喜欢菲利普·罗斯。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女人都会有这种陈腔滥调。可他却说,不,菲利普·罗斯非常优秀。他曾经做过一场关于菲利普·罗斯作品的公开课,结果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来了,而且还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罗斯听完了整堂课,中间还不时点头,两条长腿交叉,又分开,又再次交叉。下课后,他一言未发,直接起身离开了。
“他觉得怎么样?”我问,“他生气了吗?”
路易斯说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将永远是他心中的未解谜团。
我说:“菲利普·罗斯的腿很长吗?”
他说:“不如我的腿长,小瑞。”
偶尔调调情,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接着他问起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有个女儿,叫阿维娃。他说在希伯来语中阿维娃的含义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纯洁,真是个美好的名字。我说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选了这个名字。他又说,这个名字不常见,我不认识叫阿维娃的人,只听说过那个给国会议员莱文惹麻烦的女孩。你还记得那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丑事吗?
“嗯。”我说。
他说:“那件事不仅败坏了南佛罗里达和整个犹太裔人群的名声,还抹黑了政治人物,对整个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丑事。”
他说:“你真的不记得了吗?2001年那会儿这里的新闻节目整天都在播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把她淡忘了。”
他说:“我实在想不起她姓什么了。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告诉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莱温斯基没两样。那个女孩明知他有家室还要勾引他。依我看,她要么为了权,要么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她长得就是一副风流样,身材丰满——就是那种人人都会夸她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人——勾搭上莱文这样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很神气。我对这种人一点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么来着?”
他说:“真是太可惜了,莱文一直是个不错的国会议员。要不是那个小姑娘坏了事,他说不定会成为第一位犹太裔总统。”
他说:“你知道我最同情谁吗?她的家长。”
他说:“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怎么了。你说,谁还愿意雇用她?谁还愿意娶她呢?”
他说:“格罗斯曼!阿维娃·格罗斯曼!就是这个名字!”
于是我说:“就是这个名字。”
我找借口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我让服务生把没吃完的海鲜饭打了包——这里的海鲜饭很好吃,一人份又实在太大了。有些餐厅会在藏红花上偷工减料,但是大虾餐厅不会这样做。海鲜饭不能用微波炉加热,但放在炉灶上热一下还是很不错的。我说,我们平摊饭钱吧,路易斯说他正要付账。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只有当我打算跟一个男人再次约会时,我才会让他请客。罗兹常说我这种做法不知该算女权主义,还是与女权主义背道而驰。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基本的礼节。
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他说:“刚才在饭店里是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吗?我感觉气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变了样。”
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你而已。”说完便上了车。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滩地带,有三间卧室。我在家里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对家中的一切都很满意——这就是独居最大的好处。即便你嫁给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医生,他也会插手诸如家居装饰的事。而他的意见通常是“我想要一张更有男子汉气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装遮光窗帘,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规律”,还有“这个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脏啊”。而现在,我的沙发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羽绒被是白色的,厨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会脏,因为我用得很小心。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临近低谷——尽管生活有诸多不顺意,但在房地产这方面我运气总是很好——如今这套公寓的价格已是我买下时的三倍。倘若我把它卖掉,可以赚上一大笔,不过说实话,卖掉了我又能去哪儿呢?你倒是说说,我还能去哪儿?
阿维娃小时候,我还没离婚,那时我们住在城市另一头,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纳风格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茂林会所——一个封闭式的社区。如今我不在那里居住,我终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几扇大门一直让我心里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顿,我们该提防谁呢?不管怎么做,茂林会所里还是时常有人遭抢劫。那些大门就是用来招贼的。越是门禁森严,外人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值得这样大费周章地防护。不过我正是在茂林会所结识了罗兹,可以说不论我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是在那里与莱文一家相识的。他们搬进来的时候阿维娃十四岁,在读高一。
我们与亚伦·莱文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声望不高的州众议员。他的妻子艾伯丝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是南佛罗里达医疗集团的内部法律顾问。罗兹给亚伦·莱文起了个绰号——“犹太超人”。说实话,他长得的确很像超人。他只穿着运动鞋身高就有两米,一头黑色卷发,蓝绿色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开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个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礼服衬衫,也穿得起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制服——那副肩膀足以胜任这样的角色。他比我和罗兹小几岁,但年龄差距不大,所以罗兹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应该试试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丝则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却很粗壮——小腿和屁股很粗,膝盖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费多少精力才能让那一头棕色卷发长期保持笔直的金色“波波头”发型。罗兹总是说:“气候这么潮湿,哎哟,梳那个发型简直是疯了。”
说实话,我也曾试着跟艾伯丝交朋友,可她就是不为所动(不仅我如此,罗兹也试过)。我和迈克请他们到家里吃过两次晚饭。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尽管开着空调,穿着DKNY露肩连衣裙,我还是汗湿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枫糖浆烤三文鱼。这道菜不难做,先腌十五分钟,再烤三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丝从来没有回请过我们,我也就领会了她的意思。再后来,阿维娃读高三时,亚伦·莱文要参加国会竞选,他们一家便搬去了迈阿密,我以为自己从此不会再与他们有瓜葛。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个邻居,但只有少数几个才能成为罗兹·霍洛维茨那样的朋友。
然而在我脑海萦绕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罗兹,而是莱文夫妇,直到电话铃响的那一刻,我还在想着他们。打电话的是公立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问我是不是艾斯德尔·夏皮罗的女儿。她一直想联系妈妈,问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为幸存者纪念日致辞,可是妈妈既没回短信也不接电话。我向她解释,大约六个月前,妈妈患上了严重的中风,所以不行,艾斯德尔·夏皮罗没法出席幸存者纪念日。今年他们只能找其他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了。
历史老师哭了起来——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心生厌烦——她说要把幸存者聚齐越来越难了,即使在博卡拉顿也不例外——这里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犹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这里是全世界犹太民族气氛最浓的地方。她说,二十年前她发起幸存者纪念日活动时,幸存者还很好找,可是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过癌症,躲得过犹太人大屠杀,死神早晚也会追上你。
这天下午,我到疗养院去探望妈妈,那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学校食堂与死亡的混合气味。妈妈的手绵软无力,左半边面孔耷拉着。依我看,没什么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风的样子。
我告诉她,有个唯唯诺诺的中学老师在找她,妈妈努力地想说话,但只发出了几个元音,没有辅音——或许是我这个女儿不称职,反正我没听懂。我告诉她,这次约会原本非常愉快,可那个男人突然开始对阿维娃说三道四,结果不欢而散。妈妈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我说,我很想念阿维娃。我知道母亲无法回答我,所以才这样说。
我正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妈妈的妹妹梅米来了。梅米是我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但有时候她这个人不太可信。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公平。与其说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说是我不相信所有的乐天派和所谓的幸福感。梅米张开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时候,我和弟弟把这样的手臂称作“哈达萨臂”),告诉我母亲曾问起过阿维娃。
我问:“她究竟是怎么问的,梅米?”因为妈妈根本不能说话。
“她说了她的名字。她说‘啊——喂——哇’。”梅米坚定地说。
“整整说了三个字?”我不太相信。再说,妈妈说的词听着全都像“阿维娃”。
梅米说她不想跟我争论这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八十五岁的妈妈策划生日聚会。梅米还没想好在哪里举办聚会。在这里?尽管妈妈住在这儿,但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去别处?妈妈的身体不知能否经得起折腾。梅米自然觉得换个环境聚会更好,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或者去米兹纳公园那个有早午餐的饭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实在太美了。”梅米说。
我说:“梅米阿姨,你真的觉得妈妈想要办聚会吗?”
梅米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亲更喜欢聚会的人了。”
我不禁怀疑梅米和我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和爸爸过得幸不幸福。“他很会赚钱,对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于幸福,”母亲说,“那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我第一百万次意识到,做一个女人的妹妹与做她的女儿是完全不同的经历。
我说:“梅米,你真的认为现在是办聚会的好时候吗?”
梅米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见过最可怜的人。“瑞秋·夏皮罗,”她说,“任何时候都是办聚会的好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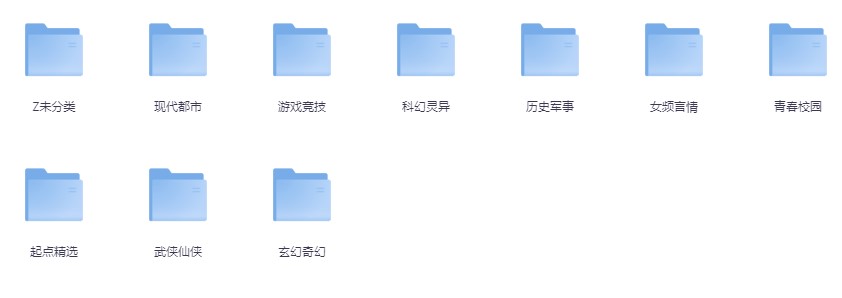





请先 !